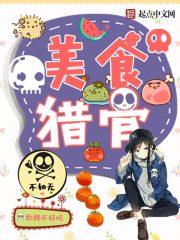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它也去 > 第23章 报应来得好快(第1页)
第23章 报应来得好快(第1页)
她诧异地看向小槐,那个黑小瘦弱的姑娘,不知什么时候长开了,脸盘圆润白嫩,微勾着头,突出的一点小下巴显得秀丽又柔弱,白皙的脖颈下不知隐藏了多少的风情,令人忍不住想要伸出手去,抬起她的脸来一览全貌。
肩背柔弱纤细,腰身盈盈一握,阿七恍然大悟,这孩子也十八了,都怪自己忙起来疯子似的,疏忽了身边的人,居然没发现她已经长成,而且早到了嫁人的年纪。
她舒了口气,摸摸腹部,还有一个月临盆,真是站也站不住,躺也躺不住,坐久了还喘不过气来,都说孩子是讨债的,果然不假,自坐了胎就开始折腾人了。
以己及人,她也该成全了小槐,将她风风光光嫁出去,若是那男孩上进,她也可以提携起来,给陈杏做个帮手。
阿七思谋的当口,小槐娘已经爬起来扑倒在老太太脚下了:“老太太,大慈大悲的活菩萨,救命啊,少爷子嗣单薄,小槐有错,腹中的孩子好歹是陈家子孙,求老太太给条活路啊?”
欲要起身的阿七又坐了回去,冷眼看着小槐娘,第一次发现这个女人还真是唱念做打样样俱佳,口口声声的,竟是说小槐怀了陈根的孩子。
老太太一愣之下,喜色泛上脸颊,刚要说什么,一眼瞧见阿七铁青的脸,再看她如鼓般的腹部,犹如热中被泼了一盆冷水,立时清醒过来,赶紧打发了身后的亲眷,关起门来处理内务。
阿七气得腿软,撤了把椅子坐到当院儿里,俨然三堂会审的主将。她将眼神投向陈根,陈根没有勇气与她对视,赤红了脸躲躲闪闪就是不看她。
看来小槐娘说的是实情了,小槐跟陈根,他们俩居然滚到一起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阿七直想笑,扯了扯嘴角却出不来声。
深呼吸几次,才找回声音,嘶哑着吐出一句:“叫你阿爷来。”
离她最近的陈平,一直拉着妹妹的手坐立不安,小槐娘儿俩的异常,父亲的躲避,母亲难看的脸色和她抖个不停的腿脚,那紧紧抓着椅子扶手的手上绽露出的青筋,都给她一种诡异的感觉,令她害怕。听到母亲的吩咐,她拔腿就走,还不忘拉上妹妹陈安。
陈平姐妹一离开,小二就靠上前来,卧到阿七的脚边。脚边依来一个软软的东西,渐渐热乎起来,阿七抖动的双腿才慢慢停住,呼吸也渐渐顺畅起来。
都说六月的天小孩儿的脸,十月的天也不遑多让,才刚碧空万里,不过一会儿的功夫,阴云便从四面笼了过来,太阳很快被遮蔽起来,天地之间只剩下穿梭的风,还在试图驱赶乌云,却不料那愁云,竟是越赶越聚拢,直重重压向人的心头。
老太太虽然没有出言力挺小槐,也示意她不必再跪着了,可见对她腹中的孩子还是很看重的,毕竟小槐娘有一句话说到她心里去了,陈根子嗣单薄!
子嗣,才是重中之重,子嗣,也才是致命伤。
阿七腹中的只要一天没有落地,性别没有明确,她就不能放心,谁会嫌弃孩子多呢?子孙绕膝是她多年的梦想,只要是她的重孙子,管他是从谁肚子里爬出来的呢。这一刻,她的心无比地坚定,任谁说什么,都不能动摇分毫。孙媳妇也不限于一人,重孙子更是多多益善。
阿七再次看向陈根:“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虽然心底已经有了答案,可她还是期待出现转机,哪怕仅有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她也要争取,即使所有的可能统统化为零,她也要听他亲口说,内心的期冀,只有他亲自打碎才能让她认清现实。
“……”
陈根的逃避让她觉得万分凄凉,又格外茫然:“这么说,是真的了?你瞧上了她?莫非你忘了,她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呐,啊?你瞧上她什么?”
“……”
“哈哈,哈哈!真是好笑,太好笑了……”阿七笑着笑着,把自己给笑哭了,她仰头看天:“报应来的好快……”乌云滚滚而来,仿佛她嘴里的“报应”。
“你好啊,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一斧头砍得准,砍得狠,直接砍到我心窝里了,哈哈,没想到腌菜帮子一样的陈根,报复起人来也是这么的快准狠啊,你都不能等到我把孩子生下来……好,好,既然你瞧中了她,我们娘儿几个立马给你腾位置,我这就给你腾开,是三媒六聘还是八抬大轿都随你便,我这就走,这就走……”说着,便要起身,也不知道是不是坐得久了腿麻了,起了几次居然没起得来。
陈根听她要离开,才着急起来,嗫嚅着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喝多了,我真喝多了阿七,你信我,我不是有意的,你别生气……”
阿七抬手将陈根推了个倒仰,跌坐在地,她还要再踢几脚,奈何腿有千斤重,居然没提起来,挣扎中差点将椅子倒翻,吓得陈根不顾自己还坐在地,猛扑上去抱住阿七的双腿稳住椅子。
阿七发起疯来陈根唯恐避之不及,此刻情急之下他居然忘了怕,阿七月份已高,若是跌过去后果不堪设想。
天色似乎没刚才那么暗沉了,零星的雨点儿稀稀拉拉砸将下来,地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个小暗点。
老太太退到了屋檐下,小槐娘也扶着小槐避了起来。陈根还跪在阿七跟前,任老太太厉声喝骂也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