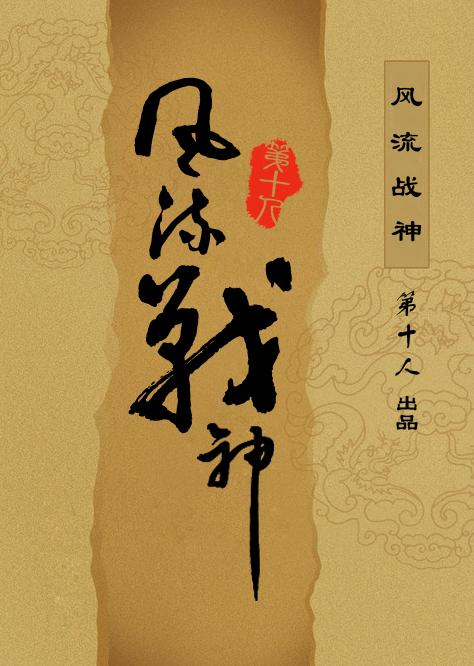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如果没有穿越这件事会怎么样 > 第57章 窗外的鞋印(第1页)
第57章 窗外的鞋印(第1页)
靳若南上午早朝以后就没回来过,下午晚一些回府以后,或许是听到什么风声,就带了烫伤药行色匆匆地跑来我的房间,却见我和明月悠闲地坐在桌前喝着下午茶,完全没有伤者该有的样子,脸上的担忧少了一半,却又一眼就瞟见了桌上,我想扔又中途放弃地薄露润玉膏,脸色在一瞬间变得复杂,且带着质疑,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明月一眼,明月就心领神会地退出了房间,然而不等我收好,他便自行入座拿起瓷瓶打开木塞,放在鼻下闻了闻,随后放下。
“薄露润玉膏,姐姐这里怎会有此物?”
“应该是宫里那位齐太医给的药,出现在这儿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开始风卷残云地吃点心,咀嚼的空档找胡乱撒了个谎话敷衍了靳若南。
“爹请了齐太医过府?”
一说到齐太医,靳若南的表情立即凝重起来,一把拉住我还抓着荷花酥的右手,飞快掀起我的衣袖,那通红的烫伤遍大剌剌地呈现在空气中,皮肤被布料摩擦过去,痛得我“嘶”地倒吸一口凉气。
靳若南的眉间皱成了三座小小的山川,一双漆黑的眸子恨不得落在我烫伤的皮肤上,这副担忧的神色和小南几乎一模一样:“明月只是区区下人,母亲要为难她那便是她的命,姐姐又何苦出手遮挡,我这一日不在家中,你竟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没想到失忆也改变不了你这爱乱出头的毛病。”
我往回缩了手,继续吃我的荷花酥,口齿不清地说:“我这副模样怎么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和二娘素来不和,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就算你在家里,也改变不了什么。”
靳若南的声音变得有些沉:“看来姐姐就算失去记忆也没能彻底忘记与母亲积怨已久,当真是深入骨髓啊。”
我吞下手里最后一口荷花酥:“段。。。。。。二娘是你和靳若棉的亲生母亲,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太为难的,以后在家里你们能不理我就不要理我,省的你娘不高兴。”
“你是这样打算的吗?”靳若南听了我的话,情绪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以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嘴里塞满了马蹄糕,说不出话来,只能肯定地点点头,心想这马蹄糕味道真不错,改天一定要亲自去厨房学习学习,这技术带回二十一世纪做私房甜品生意,应该会非常火爆吧。
“我的小微姐姐,又开始同从前一样,讨厌我,拒我于千里之外了吗?”
靳若南这副预料之中的委屈表情是怎么回事。
又?
我现在怀疑过去靳若微待靳若南不好,完全是看在段冷玉的“面子”上,其实靳若南这样的人,对我这么好,再加上他有着和小南一样的面容,我没有理由和他有什么隔阂,想到小南,眼前的人便和小南现代短发的样子重叠起来,我的眼前一阵发花。
“不一样。”
我于心不忍,闷声反对,声音有些低,几乎是无意识地说:“沈还寒永远不会讨厌小南。”
只要你还是小南的那一张脸,我就永远不会距你于千里之外
靳若南突然开心地笑出了声,像摸小狗似的在我头顶揉了一把,主动递过来一块酒酿饼:“姐姐应当永远记得这句话,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要讨厌我。”
“放心吧,不会的。”
可是靳若南,你恐怕误会了,我是我不是靳若微,你是靳若南却不是小南,如果有朝一日真正的靳若微回来了,我也不能左右你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靳若南把自己带来的烫伤膏收了起来,扫了一遍我的桌面,把我面前的茶水端起来直接从窗口倒了出去,又把五花八门的糕点连盘子一起端到桌子另一侧。
“烫伤就莫要喝茶水了,当心伤处变黑,还有这些糕点,大多是糯米所制,少用一些,积食反而得不偿失,姐姐,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明月如此懈怠姐姐吗?”
我这头发挺好的,午休过后,我就随便梳个马尾辫,也没那么多讲究,这发型是和古人格格不入,但也不至于那么不堪入目吧。
我从靳若南手里抢来一块定胜糕:“这头发我自己梳的,别苛责明月,你怎么这么啰嗦,我是长姐还是你是长兄,说得我像生活不能自理似的。”
靳若南一本正经地说:“若有来世,我倒情愿生为长兄,自小开始照拂姐姐长大,姐姐虽长我一岁,但我希望姐姐如同幼童一般无忧无虑。”
我又不是智障,十六七岁了还和幼童一样无忧无虑。
靳若南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呢?
我记得小南刚好长我一岁,更加惊恐的是小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幸好我生为兄长,可以照顾你长大。
嘴里的定胜糕突然不香了。
靳若南和现代的小南说这话重合度未免也太高了吧。
“你这话,我好像听谁说过……。”
靳若南噗嗤一笑:“谁还会对你说这种话,难道姐姐在外面还有一个弟弟不成?”
别说弟弟了,我连爹妈都没有……。
我想了想,也觉得是自己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