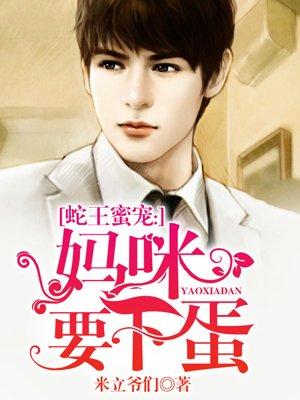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西岸三字代码 > 第45页(第2页)
第45页(第2页)
江汀低着头,贺川站着。两人一高一低,谁也不说话。
最后贺川叹口气,把削好的苹果放盘子里,“还想考北京吗。”
江汀摇摇头。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贺川,如果可以,这辈子都不要再来北京了。
“失个恋,摔成这样,连舞蹈学院都不想考了。”贺川死死攥着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就这么喜欢?”
喜欢。
这个词从贺川嘴里说出来分外讽刺,江汀没忍住鼻子一酸,眼睛红红地咬牙说:“对,就这么喜欢。”
“江汀,”贺川从牙缝中一字一句地蹦字儿,“你他妈要艺考了知不知道。”
江汀咬着嘴唇不出声,贺川直勾勾盯着他,仿佛要把他看穿,“还跳吗。”
房间里气氛降到冰点,无人说话,连呼吸都很小心。
“说话。”贺川终于忍不住,掰过江汀的脑袋,拖着他下巴,“还跳不跳。”
作者有话说:
我哭tt
p-是,我没资格
这么近的距离,如果不是贺川已经心有所属,他们或许可以接吻。
江汀晃晃脑袋,可悲自己怎么到这时候还不忘记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
然而他的摇头被贺川误解了,对方语气冷得吓人:“你当初指甲被踩劈了也说要接着跳,光练功那些苦就吃了十多年,现在就为了这么点破事儿,不跳了?”
江汀慌忙摇头,哭得说不出整句:“没有……不跳。”
他这么喜欢跳舞,怎么可能为了这种事情放弃。
“就这么跳?”贺川抬手一挥,几滴不知哪来的血滴在被子上,可谁也没注意那点血迹。
江汀实在委屈得不行,贺川就知道责怪自己,他也就能骂自己。
凭什么啊,对人家姑娘就笑呵呵的,对自己就凶成这样。
没一个人真正问自己究竟想的是什么,现在脚摔成这样又不是他想的,自己都够难过了,还凶。
江汀越听越气,终忍无可忍,猛地掀开被子,冲贺川吼道:“对,我就谈!我爱给谁送花给谁送花!你又是我什么人啊,管得着吗!”
贺川被喊愣了,他最近忙着打工处理他爸的烂摊子,接到消息后连鞋都没来得及换,实验室火急火燎跑到医院,结果江汀居然跟他划清界限。
“江汀。”贺川冷着脸,“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江汀气得发抖,一边哭一边说:“我当然知道!我不但要知道,我还要去找她,还要跟她复合,我们天高地远好一辈子!”
“行。就想早恋是吧。”贺川往后退,血沿着他的指缝一点点流,话从牙缝中一点点挤出,“你以为我想管?我愿意在这儿给你牵线搭桥?我是怕,等会你爸妈过来——”
“你少拿爸妈压我了!”江汀忽然拔高音量打断他,“贺川,他们给你一间房住,你还真把自己当我们家人了?户口本上有你名儿吗,你就敢在这教训我!”
屋子里足足静了三秒,江汀吼完自己都愣了。他从小就没受过这种罪,谁不是把他当宝贝似的供起来,所以被刺激过的脑子一下没转过来,他就想用最伤人的话刺激回去。
贺川迟缓地问:“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泼出去的水没有收回的道理,江汀仍在气头上,红着眼睛,一字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训我。”
“是。”贺川静静地靠在墙上,忽而自嘲地笑了声,“我没资格。”
门砰地一下合上了。
人显然是带着怒气走的,江汀本人也不清醒。
他盯着杯子上的血迹看了许久,怔愣地抬起头,发现床头柜上摆着削好皮的苹果。
江汀这才意识到,刚刚正在气头上的贺川似乎为自己准备好了水果与鱼汤。
以及,那双一直攥着拳的手,应该是在削皮时被割伤了。
江汀张了张嘴,想叫住贺川,让他进来包扎一下。可是窗外倚着的身影好落寞,还在举着手机打着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