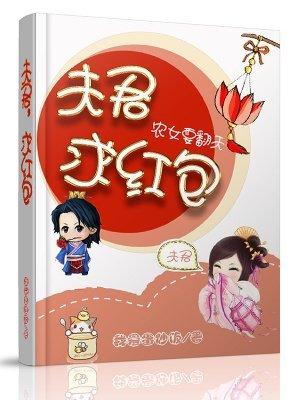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盛宠之下耳元笔趣阁 > 第101章(第1页)
第101章(第1页)
从苇河乘船南下,穿过巫峡,萧山,十日之后,便能到江南。
站在围栏里,湿润的山风拂过面颊,撩起宝仪耳畔发丝。她长的白,黑发在颈子上蜿蜒,很是惹眼。即使隔着层兜帽看不清脸,和她搭话的乡下小哥也结结巴巴的:“姑娘可是要下江南?”
“正是。”
小哥鼻尖充斥着一股暗香,他失了神:“姑娘为何要下江南去?”
傅宝仪没有回答这句话。
她问:“船何时启程?”
风一吹,小哥就醒了,他道:“今日萧山下了暴雨,水涨船高,暂时走不了。得等到晚上才行。”
“好。劳烦你,船什么时候开动,知会我一声。”
父亲,母亲,宝柒在一间房里,舅父一间,傅宝仪自己一间。她的屋子在阴面,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翻涌的波涛,与岸边郁郁葱葱的合欢树。
傅宝仪从来没有坐过船。她胃里犯酸水,难受的紧,面色苍白坐于矮凳,伏在桌前,下巴埋在臂弯里。
绿芝敲了敲门,放了壶烧开的茶水:“姐儿,请喝些茶,喝了茶就没那么难受了。”
傅宝仪点头,病怏怏的:“好,你且放下。今夜地方小,我们便同榻睡吧。”
绿芝说好,去打了盆热水来,拿着帕子,给宝仪擦了擦脸,见她如此虚弱,心疼不已:“姑娘受苦了。”
傅宝仪朝她笑了下:“不过十日,很快便能到江南。那里风景秀丽,离上京又远。等到了江南,便好好过日子,哪里都不去了。”
绿芝红着眼点了点头,扶着宝仪到榻上,给她掖了掖被角:“奴婢去看看柒姐儿。”
“去吧。”
绿芝吹灭了灯,只留了一盏小的,关上窗户和门,脚步声逐渐远了。
傅宝仪身子懒怠,很快陷入黑甜乡。
恍惚有人打开了门,进来。傅宝仪以为是绿芝,迷迷糊糊说让她快点进来,风凉。那人便进来,又没了声音。
傅宝仪懒得管那些,连身都没翻。慢慢的,她觉得不对劲儿,船舱里寂静的连掉根针都能听见。她慢慢掀开眼皮,先是看见了一双溅上了泥点子的黑面云靴,干净妥帖的玄衣纹理,再往上,一张再熟悉不过的阴恻恻的脸。
傅宝仪猛然坐起,捏着被角,紧盯着他。是梦还是真的?他怎么会追到这儿来?除非他有天大的本事。
沈渊庭居高临下,面无表情:“醒了?”
一听这声音,傅宝仪就知道,是沈渊庭,不是在做梦。很快,她出了汗,冷汗一寸一寸的往下爬,把她的后背打湿了。她努力让自己表现的平静,被褥下的腿却一直打哆嗦,她不说话,警惕的睁着眼,看着他。
沈渊庭的怒火,被这双眼睛彻底激发出来。他以为见了她的面,便会捏着她下巴质问,或者让她跪在地上认错。可对着这样一双湿润透亮又可怜兮兮的眼睛,他一腔怒火竟然无处发泄。
他质问:“你可知,擅自出逃,是死罪?”
傅宝仪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她点头,又迟疑的摇头:“我,我知道,可我已经无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