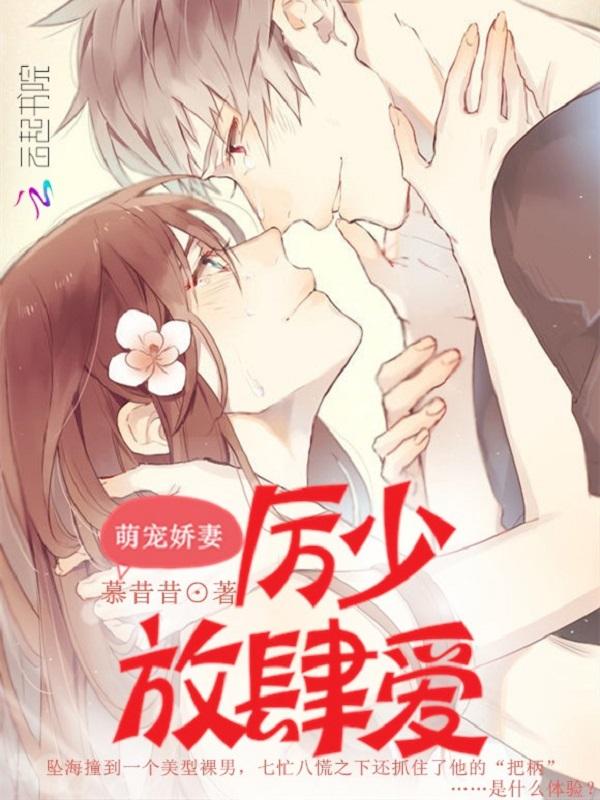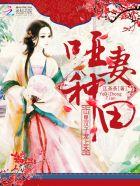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胜诉才是正义佩洛西 > 第228章 狂暴的摩根(第2页)
第228章 狂暴的摩根(第2页)
虽然这倒霉蛋距离邪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至少伯格曼可没想出“糖爹”这种伤风败俗的缺德主意来拉皮条敛财。
但不也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么?
嗯,广大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纷纷为他的死而大肆欢呼,感慨上帝终究没有抛弃正义,让对恶人的审判提前到来……
汉森本着“参议员老爷用的我用不得?”的思想,虚心向大佬学习。
并且在实践中做的更好-
-向现场观众派发铅笔信纸,大家随便写上几句后就收走,然后装进事先开好的信封中,花上两美分,然后纽约各大媒体的对外部门就头痛去吧。
有了信件抗议,当然还要电话抗议。
虽然长途电话挺贵的,但汉森是什么人?
艾比·霍夫曼的高足,掌握着全套的盗打方法,随着他到处流窜演讲,越来越多电话抗议让纽约媒体甚至纽交所都感到委屈“你们骂梅尔·菲斯特,干什么骚扰我们?”
更要命的是,这些机构的电话接线员都受过严格培训“绝对不允许挂客户的打入电话……”
这还不算。
伯克利的学生们在听完汉森和摩根的演讲后,充分发挥革命传统将武勇和智力结合在一起,又发明出更缺德抗议方法。
首先,他们攻占了一间学校的办公室。
当然是趁着国民警卫队被调走的时候,反正校园警察保安包括教授们知道,最好别和这群疯子对着干,远远见到学生大军裹着滚滚d麻青烟袭来,立刻敌进我退,好汉不吃眼前亏起来。
学生们占领办公室后,倒也不打砸抢,而是趴在电传打字机上,输入各大媒体的电传地址,然后开始发送内容冗长的抗议信。
当实在想不出新的内容时——实际上这时候信件长度已经超过20英尺长的卷尺了,可20英寸怎么能够触及那些邪恶媒体的灵魂呢?
此时米国大学生优秀的人文素养以及伯克利大学文理双修的优良教育传统就发挥出来。
从艾伦金斯堡的《嚎叫》,杰克·科鲁亚克的《在路上》,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统统成为抗议信的一部分,最后干脆有人搬来《莎士比亚全集》和《联邦党人文集》。
这种套路简单易学,既没有打砸抢也没有伴随的暴力破坏。
唯一的缺点是,校方之后得付出一大笔电传信道租用费。
但话说回来,这和破坏学校资产造成的损失比起来,那就太微不足道了。
所以,校方发现这群麻烦份子竟然转了性,守着个小小的电传打字机和还是新生事物的传真机就满足了,顿时大喜过望,干脆就懒得管了……
先进经验很快从伯克利流传开始,伴随汉森“御音放送”的磁带向整个加州乃至西海岸扩散,最终横跨合众国,又回传到了纽约……
纽黑文大草坪上的学生们顿时觉得与有荣焉,罗宾斯·纽斯和贾森·贝克两位第二国际急先锋,暂时和第四国际捐弃前嫌同流合污起来。
虽然对于盗打长途和强占电传打字机这种方式有些不满,毕竟这依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暴力和违法行为,与第二国际向来“温文尔雅”“恪守法律”的做派有冲突,但既然不是直接打砸抢,那加入也就加入吧。
毕竟申请资金的时候,也得有内容好写,若啥事儿都不敢,人家凭啥给经费?
于是耶鲁也行动起来。
反正有全套的执行方案,照着办就是了。
当然也有改良,比如发送的内容以高院判例为主,尽显耶鲁法学大宗师的派头,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此案一举奠定了司法权为三权之一的国体-实际上在此之前没人把高院当回事,甚至大法官都这么认为的-这个判例是每个法科生心目中的耶路撒冷,自然是要大力宣传。
至于马洛卡诉马里兰州,田纳西州诉约翰·斯科普斯案、合众国诉艾伦·波尔案、总检察长诉约翰·彼得·曾各案当然是应有尽有。
并且耶鲁学子们表现出了良好的法学素养和法学基本功,这些辞章华美逻辑清晰但在外人看来冗长无比的判词,他们都是直接背诵出来,根本没有去翻看判列集,这让电传的发送速度大大加快……
至于刚刚出炉的布兰德伯格诉俄亥俄案当然也在发送之例,虽然其判词的宗旨是开放言论保证公民有胡说八道的,似乎和学生们对梅尔·菲斯特的最新指控不甚相符,但谁在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