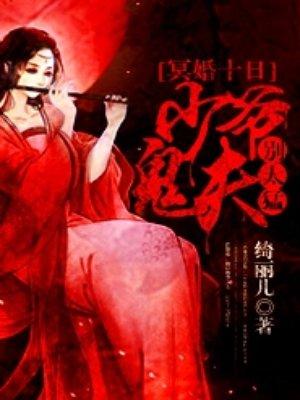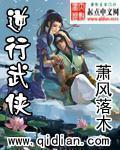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风起三国攻略 > 第43章 商议追击(第1页)
第43章 商议追击(第1页)
次日一早,张邈便将张固与公孙瓒请到了自己的大营中,三人就昨日传来的邸报进行了深入的会商。
对于袁绍将三人分兵驻守轘辕关的行为,三人心知肚明其背后的原因。袁绍此举,也是为了制衡三人,防止他们联手对抗自己。
张固之所以被袁绍排挤,心生忌惮,乃至嫉妒,皆因袁绍担忧张固立下赫赫战功,声名鹊起,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而张邈呢,想当初,会盟之始,张邈与袁绍的关系犹如春日暖阳,温馨而和谐。张邈也是坚定支持袁绍成为盟主的一员。然而,好景不长,因张固、张超父子与袁绍产生龃龉,导致张邈被发配至轘辕关,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降至冰点,宛如冬日寒冰,难以消融。
公孙瓒则因冀州之争,与袁绍结下梁子,同样被贬谪至轘辕关。命运的捉弄让这三位在轘辕关相聚,共同面对眼前的局势。
三人会商的帷幕刚刚拉开,张邈便迫不及待地说道:“袁本初传来密信,董卓大军似有撤退之意,袁绍已挥师强攻汜水关。二位对此有何高见?我们是该趁势攻城,还是静观其变?”
公孙瓒与刘备交换了一个眼神,公孙瓒缓缓开口:“张太守,昨日邸报我已览阅。洛阳即将面临攻击,董卓急于回援也在情理之中。想来轘辕关亦将遭遇同样命运,董军或将撤离。”
张邈点头表示赞同:“公孙太守所言极是,吾亦持此看法。但关键在于,轘辕关守军究竟会撤离多少?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是继续对峙,还是待袁绍攻破汜水关后,我们绕路赶往洛阳?”
公孙瓒急切地摆摆手:“不可,我们若撤退去与袁绍会师,岂不是错失良机?如今若行军回汜水关,袁绍恐怕早已攻入洛阳。一旦洛阳有失,轘辕关守军必将大部撤离,到那时我们再攻城,难度将减轻不少。”
“再者,河东的军队才刚刚渡河,尚未逼近洛阳。我们若从轘辕关迅速赶往洛阳,或许能与袁绍并肩作战,共赴国难。”
张邈闻言,眉头紧锁:“公孙太守所言虽有理,但轘辕关守军是否撤离、撤离多少尚未可知。我们得兵力攻城是否可行?若他们坚守不撤,待袁绍攻破洛阳,救出天子,我们岂不仍在轘辕关虚度光阴?届时天子大封功臣,我们却一无所有,岂不遗憾?”
公孙瓒闻言,也是一筹莫展:“这确实是个难题。不过袁本初毕竟是盟主,他未让我们改道汜水关,我们擅自行动,恐怕难以交代。”
张邈见状,心中更无主张,于是转头看向张固,问道:“安定,你为何一直沉默?不妨说说你的看法。”
张固沉思片刻,缓缓开口:“伯父、公孙太守,我料定董卓并非撤军回洛阳,而是意图迁都长安。”
公孙瓒闻言,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什么?迁都长安?这怎么可能!洛阳王公大臣众多,未经商议便擅自迁都,董卓岂敢如此嚣张?”
刘备也站起身,目光炯炯地问道:“张将军何以如此断定?莫非你在董军中有细作?”
张固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并无细作,只是我根据自己的分析所得。诸位试想,董卓若撤往洛阳守城,又有何意义?盟军一旦将洛阳包围,董卓岂不是插翅难飞?只有败亡一条路。而董贼迁都长安,则可凭借雄关险隘继续坚守。再者,联军粮道漫长,不利于几十万大军久战。时日一长,联军必然散去,董卓的危局也就迎刃而解了。”
“至于公孙太守所问的董卓敢不敢的问题,他连皇帝都敢废黜,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只要用刀架在王公大臣的脖子上,又有谁能反抗他呢?”
“至于董卓是死守洛阳还是迁都长安,我们只需观察轘辕关守军的动向即可。若董卓死守洛阳,轘辕关守军便不会撤离,最多只是抽调部分兵马回防洛阳。这样一来,他们至少可以将我们三路大军挡在轘辕关外。”
“若董卓迁都长安,则轘辕关守军必将全部撤离,死守轘辕关便毫无意义。到那时,他们只会留下一个空关,将士兵全部撤走。”
“因此,公孙太守和伯父不必过于焦急。我们既不必攻城,也不必绕路汜水关。只需静待时机,便可洞悉董卓的意图。”
刘备听后,眼含热泪,悲愤交加:“董贼若真迁都长安,还如何救出天子?汉室危矣!”张固见状,只能尴尬地劝慰道:“玄德公切莫如此。我们只需尽己所能,为汉室尽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