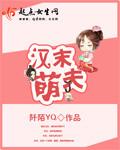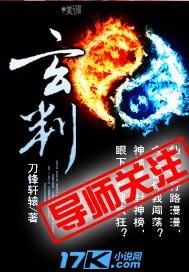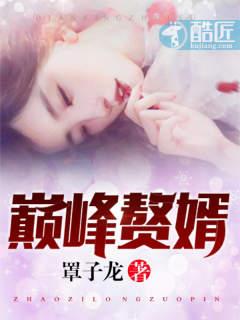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春秋时期隐者的来源 > 第105章(第1页)
第105章(第1页)
不仅如此,《左传》紧接着还解释了孔子之所以删去“费伯帅师城郎”这一记载的理由:这一事件是费伯私自行动的,并未得到鲁隐公的指派。于是,这一“不书”也和“书”一样暗含着孔子的某些微言大义,而这里的微言大义又是《公》、《榖》两传所未能阐发的。
读者如果把这几层意思一一体会出来,很容易就觉得《左传》比《公》、《榖》两传距离孔子更近,而这就关系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诸如学派的地位和学者的职位之类,所以,这个说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严谨的学风和纯真的信仰也许在争议当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尽管这都是我们难以揣度的。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道:这种所谓“不书”的体例都是刻意编造出来的,显得左氏亲眼见过史稿原本,非《公羊传》所能及。殊不知《春秋》对于筑城这类事是一定要加以记载的,以示重视民力之意。再说,如果费伯这次筑城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动,《春秋》自当在文辞上做做手脚,以示微言大义之贬,决不会仅以一个“不书”了事。909
刘逢禄虽然论之得力,但《左传》一派的学者也自有一套说辞。当初杜预就曾引《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国君的举动必定要书之于史册),说这是史官记事的规矩,孔子这次的“不书”也是因袭了这一惯例。——这就意味着:即便是鲁史旧文,其中也不会有费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动的记载。孔颖达为之作疏,越发强调了这层意思,说旧史不书,《春秋》也跟着不书。910——这就意味着,《左传》的这条记录另有资料来源。
但是,若依杜、孔之说,马上又会出现问题:既然“君举必书”,但与《春秋》经文一作对照,难道国君每年所作之事都会如此之少吗?再者,《左传·襄公七年》也记载过一次费邑筑城的事情,这时的费邑是季氏的私邑,由南遗管理,掌管徒役的叔仲昭伯为了向季氏讨好而去打通南遗的关节,说:“请修筑费邑的城墙,我给你多派劳动力。”于是季氏修筑了费邑的城墙。911
叔仲昭伯对南遗说的“请城费”,很难理解为请南遗向鲁君请命修筑费邑的城墙,那么这次城费自然是“非公命也”,《春秋》却没有一视同仁地予以“不书”。至此,《左传》的前后文便难以自洽,再来考察隐公元年这次“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的记载,所谓“不书,非公命也”的解经之辞就显得多少有些牵强了。
(二)费与费有别
钱牧斋途经费县,道中赋诗:“驱车入鲁吊遗黎,宗国相传事可悲。歌凤有人供放逐,斗鸡无相系安危。申丰锦去邻争羡,阳虎弓还盗亦嗤。唯有汶阳田下水,至今流恨绕凫龟。”912通篇都用春秋鲁事,多与费地有关。
费伯帅师城郎。这位费伯是鲁国大夫,不姓费,而是和周天子、鲁隐公一样姓姬,费是他的采邑,在今天山东省鱼台县西南。费,在春秋时代也算是个颇为有名的地方,《论语·雍也》讲过鲁国权贵季氏想让孔子的学生闵子骞作费邑的地方官,闵子骞不愿意干,宁可逃跑也不愿接受,913《论语·先进》还曾说起子路要让子羔作费邑的地方官,惹得孔子很不高兴。914更著名的是《论语·季氏》里那段:“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季氏将伐的这个颛臾,就“近于费”,大约让季氏觉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起意要把它拿下来。《论语·阳货》还有一段经学疑案,通行解释是说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想招揽孔子入伙,孔子还真动心想去,于是说出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句千古名言。915
《左传·僖公元年》有“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说鲁僖公把汶水以北之田及费邑赐给了季友,这和《论语》里的相关记载倒是可以合拍的。
但费地的知名,渊源还要比上述这些更早。《尚书》里边有一篇《费誓》,内容一般认为是鲁国始封君(或第二任封君)伯禽916平定徐戎、淮夷之乱,在费地誓师大会上的演说词。917孔安国《尚书传》注音说:“费音秘”,释义说:“费,鲁东郊之地名”。
费,不读fèi而读bi,再看《左传》,杜预给费伯的费字注音,说:“费音祕”《汉书·五行志》颜师古的注释里也有提及:费,是鲁国的城邑,读音是“秘”。陆德明《经典释文》在《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这里注释“费”字,说:“音祕,邑名。”9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费伯这里注释说:“‘费’,《释文》音‘秘’。费伯,鲁大夫。费亭当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西南。”919
前后一联系,这个费地看来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伯禽曾经在此誓师,后来这地方成了费伯的采邑,再后来又归了季氏,但季氏名下的费地总出麻烦,不得不频繁更换地方官,甚至还有个公山弗扰据费邑而叛乱。——元代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就串起过这些资料,给了我们一个笼而统之的印象。920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谈到费地人文地理的历史脉络,说这里是“古费国也”,后来即有“费伯帅师城郎”,再后来又作了季氏的采邑,汉代为费县,属东海郡,从宋朝到隋朝都属琅琊郡……西北八十里的蒙山就是老莱子的躬耕之处,西北七十五里是东蒙山,即《论语》所谓“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之东蒙。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