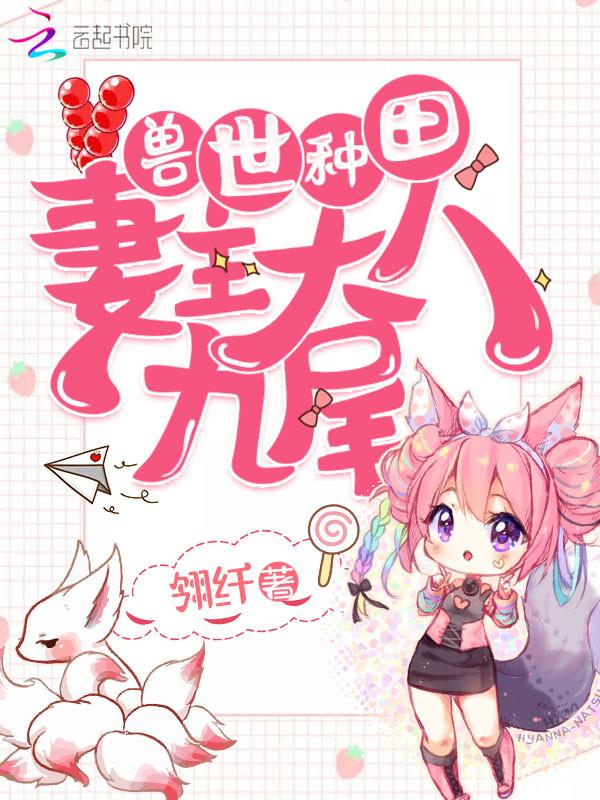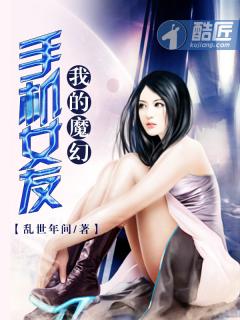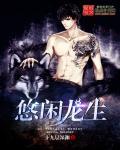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春秋时期隐者的来源 > 第165章(第1页)
第165章(第1页)
政治之道,首在人伦,“修己以安人”,1487这是儒家的一个普遍观念。真德秀《大学衍义》在修齐治平的序列上仅仅论及齐家,因为“四者(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1488朱熹曾经概括《春秋》的开篇大义,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1489——《春秋·隐公元年》寥寥几件事,便述尽了君臣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和兄弟关系,这些既是切身小事,也是政治要诀,故而“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按部就班,顺理成章。
那么,如果再问一步:当叔段已经具有京邑、并吞廪延之后,乱象已生,这时候郑庄公又应该怎么做?换句话说:如果在这时候把大舜放到郑庄公的位置上,他又会有什么妥善的解决之道吗?
——苏轼就曾经议论过这个问题。作为宋代蜀学的领军人物,苏轼虽然没有《春秋》方面的专著,倒是有过一些相关散论的,其中便有一篇《论郑伯克段于鄢》,认为到了叔段乱象已生的时候,就算大舜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叔段是非杀不可的。《春秋》之所以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称“郑伯杀其弟段”,是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就算圣人也无法保全兄弟之情。夫妇、父子、兄弟之亲,都是天下之至情,至情之间酿成这般相互残杀的局面,定非一日之寒。——郑庄公到底应该怎么做?苏轼品评“三传”的解决方案道:《榖梁传》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矛盾之深都已经到了这种田地,就算真的缓追逸贼,恐怕也保全不了亲亲之道了。所以说,真到了这种时候,就算圣人也会杀弟,但圣人显然有办法防患于未然,不会使事情恶化到这般地步。《公羊传》说“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又分析当国、内外云云,见识短浅。《左传》认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敎”,若要探求圣人的深意,《左传》还是比较可取的。1490
看来,即便大家都能同意用大舜和周公来作参照系,得出的结论也未必相同。甚至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据《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李世民的手下劝他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说是那两人早就想除掉李世民了。见李世民迟疑不决,大家就引大舜为例,问道:“您觉得大舜这人怎么样?”李世民自然是一番夸赞,说大舜既是孝子,又是圣君。大家再问:“大舜当初被骗到井里的时候,如果没能侥幸脱身,岂不就被困死了,哪里还有被人夸作孝子的机会?被骗到谷仓上的时候,如果就那么被烧死了,又怎么可能在将来成为圣君?小委曲可以忍一忍,但大难可一定要躲一躲!”李世民这才下了决心,要把李建成和李元吉除掉。1491
周公诛管、蔡的例子也被这些人援引过。《旧唐书·房玄龄传》载,李世民到李建成那里吃饭,中了毒,一众手下大为惊骇,房玄龄便和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矛盾已经化解不开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出大乱子,到时候不要说秦王府,就连国家社稷都会动摇,那还不如学周公好了,古人说“为国者不顾小节”,该下手就得下手。1492
同样是大舜和周公的例子,重要的是解释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7.吕祖谦《东莱博议》:科举范文
如果不对大舜和周公的故事作出过度曲解的话,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光辉形象(尤其是大舜的形象)实在是太高大了,高大到几乎遥不可及的地步。大舜和周公被树立为了至高典范,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谁,和这两位大圣人比起来只能显出一副灰头土脸,其间区别只是灰头土脸的程度不同而已。
道德标准树得越高,现实批判也就往往批得越狠;圣人深意求得越深,诛心之论也就往往越诛越玄。种种议论,除了学者专著之外,还有大量的科举论文,要想把文章写得既别出心裁又不至于偏离官学划定的意识形态准绳,那就得把圣人深意比别人挖得更深。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怕要算是吕祖谦的《东莱博议》。
吕是朱熹的好友,曾经邀集过著名的鹅湖之会,他在东阳授课期间为学生们讲述《左传》,写下了不少科举范文,辑录成册,便是后来很著名的《东莱博议》,无论是老师授课还是学生练习作文都常用这部书。比之象牙塔里的一些专著,这部书在中国传统上发挥了更大得多的影响。
科举文章,不仅要有好见解,也要有好文笔,而吕祖谦既是经学家,也是散文家,兼具两家之长,议论经学也常常从文学角度着眼。《东莱博议》的第一篇范文就是论郑伯克段的,句式多对仗排比,议论多峰回路转,很有几分炫技的味道,而诛心的技术也被发挥到了极至: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阱,天下宁有是耶?
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雠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机而使之狎,肆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甲兵之强,卒乘之富,庄公之钩饵也;百雉之城,两鄙之地,庄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顽不灵,鱼耳,兽耳,岂有见钩饵而不吞,过陷阱而不投者哉?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