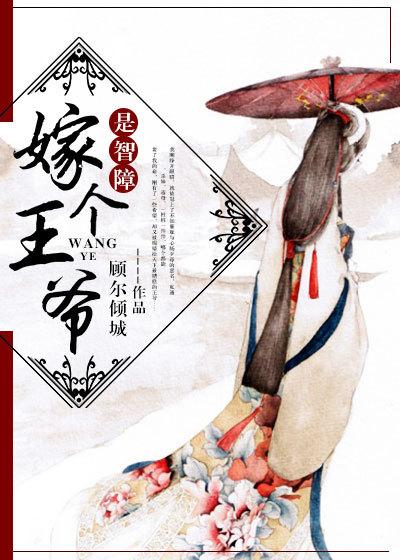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春秋时期隐者的来源 > 第177章(第1页)
第177章(第1页)
姚舜牧贯通隐公世的全部十一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不说很有道理,而且确实曲折深刻。无论他是否真的探得了圣人真意,至少为读者列出了这十一年纷繁事件的一个清晰大纲。但是,当我们回顾自汉代以来的这无数歧说,各有各的道理,却依然不知道孔子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五)清代克段解三例
胡安国的巨大惯性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李光地为康熙帝讲解《春秋》,用的底本就是胡安国的《春秋传》,经筵讲义汇编成书,即清代官学著作《日讲春秋解义》。——这些春秋大义是儒臣讲给皇帝听的,重义理而轻章句,到底《春秋》仍被看作是孔子垂法万世的政治哲学,即康熙序言里所谓的“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但是,对《春秋》这部圣人大经,康熙帝学得越深,疑惑也就越大:一是越发感觉那些所谓微言大义太离谱了,什么凡例、变例,什么称人以名还是称人以爵,怎么看怎么觉得支离琐碎、穿凿附会;二是康熙帝对程朱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而越是欣赏朱熹的平实之论,就越是不满胡安国的空疏作风;再有就是发现胡力主“尊王攘夷”,“尊王”倒是好的,可“攘夷”实在大触自家霉头。
所以,终康熙一世,《日讲春秋解义》并未刊行,而在康熙帝晚年刊行了一部《春秋传说汇纂》,书中虽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而把胡安国的《春秋传》列于“三传”之后,却对胡氏之说作了很大的删改——“攘夷”从此变成禁区。
康熙帝为《春秋传说汇纂》所作的序言里,批评了那些宗胡学者的在穿凿附会方面的不懈努力,他们研究得越深,也就离经义越远,而这部《汇纂》以“三传”加《胡传》为主,以集说为辅,凡有悖于经、传的就删而不录。——康熙帝这个标准,听起来倒很公允,但实行起来有一个很大的难度:历代经学歧说那么多,经师们各执己见,但到底谁的意见才是合于《春秋》本旨的,始终都说不清。康熙帝自己也清楚这点,接下来说:司马迁曾说孔子门下的“七十子”通过口传心授学习《春秋》,每个人的理解都不相同,在当时就没有形成定论,所此说来,后儒在千百年之后揣摩孔子的笔削之意实在太过困难了。
康熙帝毫不讳言探求《春秋》本旨“不亦难乎”,说这部《春秋传说汇纂》只是退而求其次,辨之详、取之慎,争取能对属辞比事之教有些助益而已。1578
康熙帝这么说,虽然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的自谦,但显然也明白承认了《春秋》所蕴涵的孔子真义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被发现了。
康熙帝这个说法为官学定了调子,但人们对破解《春秋》密码的热情依然不减。即便“名弧石勒诛,触眇符生戮”,1579文字狱把许多学者驱赶进了训诂考据的天地,但依然不乏有人立意以训诂考据的方式来为经典解码。这部分地是因为文字狱的威力被过分夸大了,1580毕竟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思想钳制是专制体制的伴生物,是权力集中度的函数,只要专制尚在,思想钳制就在。而满清虽然以君主个人的高度专制著称,但正如朱维铮说:“由于满洲君主贵族始终只信仰庇佑过自己祖先的守护神,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给以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当然要以奴隶不得冒犯主子作为条件。清朝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倒是溺于道统正统之类理学说教的迂夫子,便从反面递送了容忍异端及其限度的信息。正因如此,在君主高度专制的清朝,反而出现了对传统的经学诸形态逐一予以怀疑和否定的活跃思潮。”1581
求是之风及于史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甚至明确反对史家一贯的褒贬传统,1582而另一方面,即便是训诂考据,也并非仅仅只是训诂考据而已,如惠栋所谓“经之义存乎训”的宗旨,很多时候训诂考据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永远是亘古相传的那四个字:通经致用,1583尽管纯粹的训诂派也占有一方势力。1584
《韩诗外传》释儒为“不易之术也”,释六经为“千举万变,其道不穷”1585,《纯长子枝语》谓“儒为有道术之称”。归根到底,经学总在秉承着西汉传统,是术而非学,任凭世界千变万化,儒者也能从六经当中找出解决方案。如果经学从实用政治学走向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这应该算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倒退,如颜元所谓:“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自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1586
训诂也好,词艺也罢,总该为经世服务。即如四库馆臣也提出过经之义理要基于训诂、史学褒贬要基于事实的主张。1587经学作为政治学,经义之中自须体现大道,学者若把训诂打通则大道不待求而自现——王鸣盛为此作过一个比喻,说人想食甘,到市场上去买叫做甘的东西,遍寻而不获,而买了块糖吃则甘味自现。1588考据与治道的关系便是如此,此为一代之风气使然,如戴震曾论义理与训诂之关系,认为从字义之考据出发可以循序而上达于道,1589之所以要细之又细,因为圣人之道“毫厘不可有差”。1590这般义理,并非宋儒《西铭》、太极之类的想像,而是自我得之,自实处得之。1591戴又论到当时人们常说:“经学有汉儒之经学,还有宋儒之经学,前者主攻训诂,后者主攻义理。”——这确实是清代的常论,当时的学者大多轻视宋学而推尊汉学,反对宋人的空谈心性,甚至如冯班所谓“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1592而戴震说:这个说法不合情理。所谓主攻义理,难道就可以抛弃经文于不顾而凭空猜想吗?如果这样也可以,那人人都可以穿凿附会,这对经学有什么好处?凭空猜想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求义理只能求之于古经,而古经距离我们时代太远,难以索解,所以才需要求之于训诂。只要把训诂工作搞通了,古代经文的意思也就会被搞通,圣人的义理也就会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自心与之暗合的地方也自然会因之而明朗。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