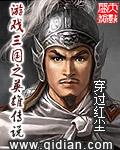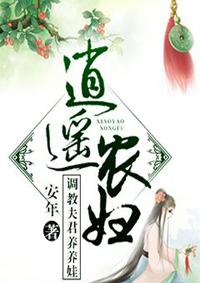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生命的两头阅读答案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我叮嘱叶田,50周年大庆之夜的灯光,一定会比我们看过的任何灯河灯海瑰丽多彩。只因在8月的试灯之夜,我已经去饱了一回眼福。
瞧那是挂于空中的明灯,五彩缤纷,天花乱坠。
看那密布于地上的彩灯,争奇斗艳,光芒四射。
让我们相约,在今年的国庆之夜,一起步入五光十色、星光灿烂的街头,去感受人间银河的美景。
(1999年9月)
第六部分
百年老店邵万生(1)
1843年,上海开埠了,成为东海之滨重要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
四面八方的人涌入上海,使得上海很快地成为一个八方杂处、百业纷陈的大都市。
在各地来到上海的人中,浙江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和份额。为什么?浙江紧挨着上海,坐上火车、搭上汽车、挤进低矮的乌篷船,熬过一两天、两三天就到上海了。在栖身上海的浙
江人中,宁波人和绍兴人又占着最大的比例,这比例至少多于杭州人、多于嘉兴人。宁波的一位旅游局长曾十分自信地对我说,我做宁波的旅游,主攻方向就是上海。因为四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宁波人。一千六百万上海人,祖籍宁波的有四百万。这些宁波人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只要四年回一次故乡,宁波每年就有一百万上海客人。说完他哈哈大笑。
我没有具体统计过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和绍兴人。但在小时候,几乎每条弄堂,我们读书的每一个班级里,都有绰号叫&ldo;老宁波&rdo;&ldo;小绍兴&rdo;的伙伴。至于平时交往中,宁波话和绍兴话,更是耳熟能详,时常往耳朵里灌的。开玩笑的时候,模仿能力强的同学,时常会惟妙惟肖地说几句宁波话、绍兴话,逗得大伙儿捧腹大笑。
可以说,宁波人、绍兴人是伴随着上海的开埠进入上海滩的。他们也像其他各地的人到达上海时一样,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口音,他们的风俗,同时带进来的,还有他们多姿多彩的吃的风味。
我想,一百五十年前,邵六钵头就是随着这么一股人流,从故乡来到上海的。
上海滩的田地变成了马路,他依靠什么才能生存呢?那个年代,上海滩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传奇,关于洋人们和买办们发迹的故事,在大街小巷里传播。邵六钵头是个聪明人,而且有离乡人共有的怀乡情结。他一定还知道,像他这样怀念故乡、思恋故乡风味菜肴的人不在少数。一路上来到上海,他必然碰到很多像他一样到上海来的家乡人。
于是他在虹口开办了一家南货店,名叫邵万兴。邵是他的姓,万兴是他的愿望,希望他新开办的店铺能兴旺,能发达,能一兴而起。这是清朝的咸丰二年,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还拖着辫子。也就是1852年。
还是我小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邵万生是一家百年老店。在上海滩,以精制糟醉食品闻名。他们按照宁波、绍兴的乡土风味,自产自销四时的糟醉食品。我一位同学,自小在山西路上长大,又是绍兴人,每当大家聚在一起闲聊,说起衣食住行,他就会眉飞色舞地给我们介绍新鲜的河虾子酱油、沈家门认姆渡黄泥螺、虾子鲞鱼、糟青鱼、鲥鱼、醉蟹、醉蚶、糟鸡。只要他一说开,就像无轨电车开出来,刹不住车。我们一个个都要被他说得口水流出来,他也不肯罢休。还要介绍什么宣城蜜枣、金华酱腿、北京彩蛋。我们忍不住问他,这些东西你都吃过吗?他会连连点头说:&ldo;怎么没吃过,从小就吃的。&rdo;
于是我就晓得,邵万生这家百年老店,开在山西路、南京路口。多少年以后也还记得清清楚楚。上世纪80年代在贵阳工作时,有同事来上海出差,请他们带邵万生的黄泥螺,总还要特地叮嘱:&ldo;你逛南京路时,走到山西路口,就找到这家店了。&rdo;
非常凑巧的是,和我在同一个知青点集体户插队落户的知青小李,家住在宁波路河南路口的弄堂里,他的父亲是40至50年代的邵万生职工。插队落户的岁月里,生活清苦,经常用辣椒、猪油淘饭吃。大家更愿意想像上海的美食,举行&ldo;精神会飨&rdo;。每当这时候,小李就会如数家珍地介绍邵万生的食品。所谓&ldo;春有醉蚶,夏有糟鱼,秋有醉蟹,冬有糟鸡&rdo;。除了介绍食品,顺便他还会给我们讲一点邵万生的历史。最早开在虹口的邵万兴,到了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搬到南京路上来了。只因随着上海的百业兴旺,人气飚升,南京路愈加繁华和鼎沸,生意更好做了。这一点更加深了我对邵六钵头这个人的印象,他不但是聪明的,还是随机应变的。搬到南京路的邵万兴更名为邵万生,意思是取其生生不息地往前发展。
春天,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新鲜的河虾大量上市,邵万生的前店后工场,就精制虾子酱油。选料采用舟山裕大抽油,苏州乡间活河虾剥子焙烘配制,故而一下子打开销路,美名远扬。上海人争相购买味道鲜美的虾子酱油来尝。
夏天,气候炎热,上海的居民大多忌食油腻,邵万生就抓住时机,趁着黄泥螺、鲜鱼的市场供应量大,就糟制黄泥螺、青鱼、鲤鱼应市。同时还不忘宁波老人们特别青睐的&ldo;三臭&rdo;,满足人们的需要。俗称&ldo;三臭&rdo;的臭冬瓜、海菜梗、臭黄豆,是标准的&ldo;闻闻是臭的,吃吃是香的&rdo;传统饮食,适时推出,亦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