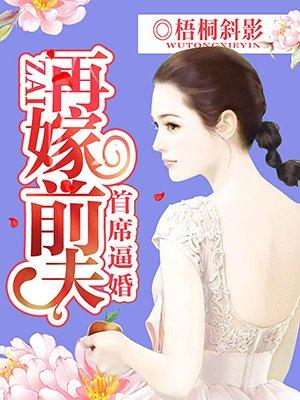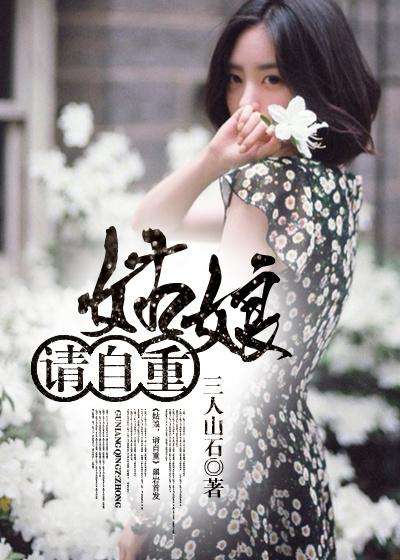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的还是女的 > 天工开物 附录 宋应星生平译文2(第2页)
天工开物 附录 宋应星生平译文2(第2页)
宋应星所叙述的锌的提炼方法是:制锌所用的原料是炉甘石(不纯的碳酸锌),把炉甘石放在泥罐中封泥加固,再逐层用煤炭饼垫罐底,下面铺薪引火。炉甘石在罐外炭火烧灼的较高温度下,发生化学分解反应,分解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从泥罐缝中逸出,而固体氧化锌又受到从缝中进入的或者是封罐时加入的碳的作用发生还原反应,而得到金属锌。
《天工开物》炼纯锌的文字记载比欧洲要早,所以,宋应星对金属锌(“倭锌”)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宋应星还指出了锌和铜按不同比例制成铜锌合金(黄铜)的方法,也是冶金史上的可贵记载,具有世界性的生产指导意义。宋应星还记载了利用金、银、铜、锡、铅、锌、汞等金属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活泼性的不同,来分离或检验金属的各种有效办法。譬如他记载把白银从含银的黄金里分离出来的办法,是利用硼砂熔点较低的特性,在分离时起助熔作用。当把金银合金熔化后,由于金(熔点1063℃),银(熔点961℃)熔点不同而进行分离,银首先“吸入土内,让金流出,以成足色”。再入铅少许,又把银钩出,这是近代冶金学中所说的熔融提取法。宋应星在论述金、银、铜的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经有了物理学中的比重概念。
《佳兵》:记载弓箭、弩、干等冷兵器和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
《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均为文房用具。
《曲糵》: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种。宋应星记载的红曲可以用于食物保存,和近代用抑制微生物生长的抗生素保存食物出于同一原理。他在叙述红曲制造时,特别强调选用绝佳的红酒糟作为“曲信(菌种)”,并加入明矾水来保持红曲菌种培养料的微酸性,以抑制其他有害杂菌的生长。这些都是发酵工艺中长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具有很深刻的学理性。
《珠玉》:宋应星本着轻视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指导思想,把它放于卷末。主要叙述在南海采珠,在新疆和田地区采玉,在井下采取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还谈到了玛瑙、水晶和琉璃等。
《天工开物》除文字叙述外,还有123幅插图,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除个别章节引用前人著述以外,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宋应星在南北各地科学调查的资料。在叙述生产过程具体技术的同时,宋应星还用“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对所述技术给以理论上的解释。这同一般的技术调查报告是不一样的。
《天工开物》这本书的书名,表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天工开物强调的是自然力(天工)和人工的配合,自然界的行为和人类活动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产物,以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科学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者是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万物。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手工业的18个生产领域中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对我国明代以前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积累起来的技术经验作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概括,并使它系统化,构成了一个科学技术体系,这是一项空前未有的创举。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用《冶铸》《锤锻》《五金》等三卷专门叙述铁、铜、铅、锡、银、金、锌等金属和它们的合金的冶炼、铸造、锤锻技术,填补了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文献空白。
宋应星是从我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全局出发,以比较的方法来融会贯通地综合研究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宋应星注重“实践”和“穷究试验”,注重时间、空间和比例的数量概念,对迷信和唯心谬论持怀疑批判态度,一洗封建时代研究学术的歪风陋习,把近代科学启蒙者所具有的那种实证精神带到了科学界中来。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完全可以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柯拉(1490—1555)撰写的《矿冶全书》相媲美。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介绍到欧洲后,欧洲人把宋应星尊称为“中国的狄德罗(1713—1784,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以编撰《百科全书》知名)”。宋应星在中国历史上,是和李时珍、徐光启、方以智等16、17世纪的卓越人物相并列的,都是明代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中启蒙思潮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曾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受到启发,又在不少地方对这本书进行了发挥。宋应星还弥补了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在手工业方面的遗漏。
公元1643年,方以智在写作《物理小识》时就参考了《天工开物》,在卷七金石部中引用了《《天工开物。附录。五金》铜条中的资料。
(五)宋应星的晚年
1637年6月,宋应星完成了他的《卮言十种》中的第八种《论气》一书。《论气》是宋应星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和《寒热》等篇章。宋应星在《论气》一书中,继承了先秦的荀子(公元前330—前227),汉代的王充(27—107),宋代的张载(1020—1077),特别是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宋应星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又返回到“气”。在形和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
宋应星把元气论和新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宋应星的二气五行之说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和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土火水气四元素说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他在气和万物之间引入了水火土金木这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
宋应星还进一步讨论土石五金的“生代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的物质成分和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和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上的。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音强度的因素等问题。
宋应星在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指出声音是气的运动,由于气与形之间的冲击而发出声音,以形破气而成为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气间冲击的强度,急冲急破。
宋应星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他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达到的距离的10倍。他认为,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很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扩散那样,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经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以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还在争论关于声音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盖里克用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声波的概念是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宋应星在研究声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1637年9月,宋应星又完成了《卮言十种》中的第九种《谈天》一书。《谈天》主要是谈日,当宋应星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认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如果认为是昨日之日,是“刻舟求剑之义”。认为太阳不但沿着它的轨道周行不已,而且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样,就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来,王夫之发挥了宋应星的这种“日日新”的思想。
宋应星还批评了宋儒朱熹(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的天人感应说观点,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
1638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已满,考列优等,随后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
1640年,宋应星任期还没有满,就辞官归里了。
1642—1643年,宋应星在奉新家居住时,当地爆发了由李肃十、肃七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宋应星曾经与兵备道陈起龙、司李胡时享等,用计谋和武力镇压了这次起义。
1643年,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这是宋应星一生担任的最高官职。宋应星担任亳州知州时,已经是明亡的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官署都被毁,他捐资努力重建,又把出走的官员招集回来,还捐资在城南买下了薛家阁,准备建立书院。
1644年初,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宋应星的心愿未遂,辞官返回了奉新。3月19日,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树上。是日农民军破内城各门,李自成乘马进城,入承天门,登皇极殿。城内人民都设案焚香迎接,于门首大书“顺民”和“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明朝的腐朽统治至此崩溃了。
4月22日,清兵进入山海关,包围了北京城。宋应星虽然早已挂冠,回到了奉新家中,仍关心国家大事,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痛恨那些汉族大官僚地主依靠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对广大人民施行民族压迫的可耻行径,就挥笔草成了《春秋戎狄解》一书,借古喻今,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1644年清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
5月15日,南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政权完全是明末腐朽政权的继续。
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和南湍兵巡道,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他在晚年决心做一个隐士。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也无意恋官,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政权,但这个政权由马士英、阮大铖擅权,内用宦官,外结诸将,政以贿成,官以钱得,有“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之谣。这个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内部就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阮大铖勾结马士英,日以党争为事,罗织罪名,排挤打击东林党人。
1645年5月,清军渡江,福王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不久,清追兵至,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后在北京被杀。宋应星和宋应升回到家乡后,阔别多年得以重逢,虽然是兄弟相见格外高兴,但国事的不可为又给他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尤其是清兵攻破南明政权后,又南下去取江西,更使他们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