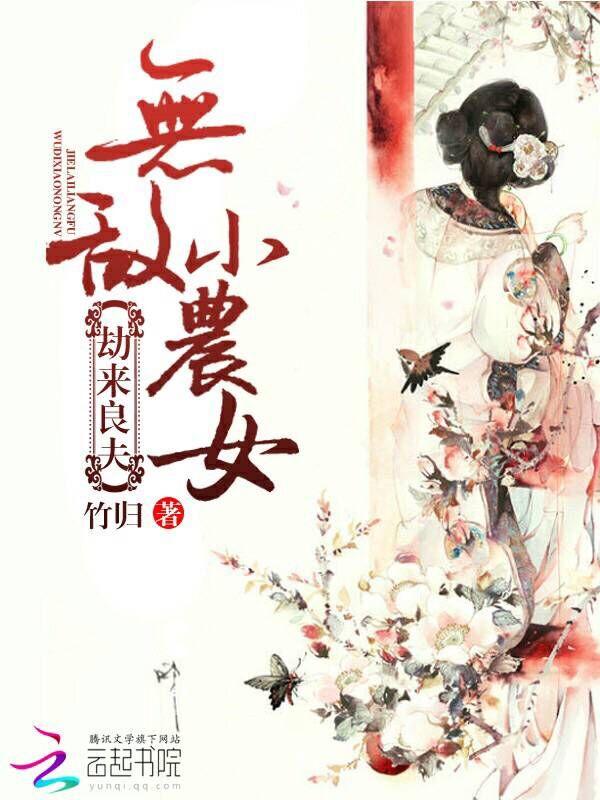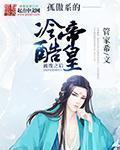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古代大儒 > 第57章(第2页)
第57章(第2页)
系事实,孔子&ldo;述而不作,信而好古&rdo;[注],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
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
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
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
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ldo;欲治《左氏》,引
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
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rdo;他是以所记历史
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志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
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
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发,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
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
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
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刘歌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
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
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
上看,是企图拉着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
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
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
&ldo;或为雅,或为颂&rdo;,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ldo;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rdo;
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
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ldo;少以通《诗》、
《书》能属文召……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欲及向
皆治《易》,……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博物治闻,通达古今。&rdo;
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ldo;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rdo;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