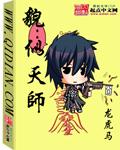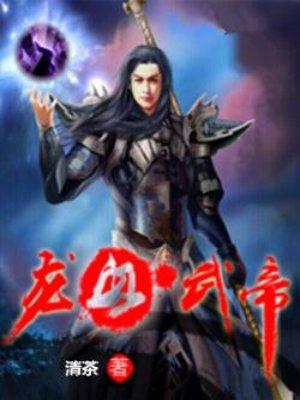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重生朱标打造巅峰大明 > 第39章 学潮涌起文改遇碍(第1页)
第39章 学潮涌起文改遇碍(第1页)
门外的喧嚣声仿佛汹涌澎湃的潮水一般,毫无阻碍地涌进屋内,瞬间将朱标的思绪冲击得支离破碎。他原本正沉浸于对一件重要事务的深思之中,但此刻却不得不被强行拉回到现实中来。
只见那心腹太监跌跌撞撞地奔入房中,满脸惊恐之色,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下来,浸湿了衣领。他气喘吁吁,连说话都变得急促而结巴:“殿。。。。。。殿下!大事不好啦!国。。。。。国子监的那些学子们竟然。。。。。。竟然罢课了!”听到这个消息,朱标心头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之前就一直担心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没想到最终还是没能避免,这把火终究还是熊熊燃烧起来了。
来不及多想,朱标霍然起身,迈开大步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一路上,他脚步飞快,如同疾风骤雨一般,径直朝着国子监飞奔而去。
当朱标赶到国子监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院内人头攒动,数百名学子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和不满。他们情绪激动,挥舞着拳头,口中高喊着各种口号,声音响彻云霄,震耳欲聋。整个国子监内弥漫着一股紧张压抑的气氛,仿佛一点火星就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爆炸。
吴学子昂首挺胸地站立于高台之上,情绪激昂、声音洪亮地发表着自己的言论:“诸位同窗好友们呐!咱们身为读书人,理应当将古圣先贤奉为师长,把经典史籍当作镜子来映照自身!然而现今,那尊贵无比的太子殿下竟然执意要大力推行那些所谓的奇技淫巧之物,难道这不是想要逼迫我们抛弃列祖列宗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吗?如此行径简直就是背信弃义、数典忘祖之举啊!”
就在此时,人群之中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殿下!您来了!”原来是有人率先察觉到了朱标的到来。刹那间,原本喧闹嘈杂的人群像是被投入了一颗巨石的湖面一般,瞬间掀起一阵巨大的骚动。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脸上流露出或惊讶、或期待、或敬畏的神情。
只见朱标步伐稳健地朝着众人走来,他那挺拔的身姿和威严的气质令人不禁为之侧目。待他走近之后,缓缓停下脚步,目光如炬般扫视过在场每一张年轻且充满激愤之色的面庞。正当他准备张口说话之际,站在一旁的宋祭酒却不合时宜地阴阳怪气地插嘴说道:“殿下啊,您瞧瞧眼前这番景象,这不正是民心所向嘛!这些莘莘学子可都是熟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之士呀,他们心中自然清楚何为人间正道,又何为旁门左道、歪风邪气呢!”
朱标并未理会宋祭酒的挑衅,反而转向吴学子,语气平和地问道:“吴学子,你为何要煽动同窗罢课?新学科究竟有何不好,让你如此抵触?”吴学子被朱标这突如其来的反问弄得有些措手不及,支吾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殿下,学生并非有意冒犯,只是…只是担心这些新学问会误人子弟!”
朱标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他那明亮而深邃的眼眸缓缓地转向站在一旁的宋祭酒,轻声说道:“宋祭酒啊,孤可是清楚地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学海无涯,唯勤是岸’。可如今,面对这些莘莘学子对于新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与渴望,您又为何要横加阻拦、阻止他们去探索呢?”
听到这话,宋祭酒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就像是被人当面揭穿了谎言一般。他有些慌乱地抬起头来,眼神闪烁不定,但还是硬着头皮强词夺理道:“老臣这么做也是出于一片苦心啊!我只是担忧这些新兴的学科尚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检验和论证,如果贸然在学府中推行开来,恐怕将来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甚至可能遗祸无穷啊!”
然而,朱标似乎早有准备。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宽大的衣袖之中轻轻取出一份折叠整齐的奏折,然后慢慢地将其展开。这份奏折仿佛有着千斤之重,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朱标手持奏折,目光锐利地盯着宋祭酒,缓声道:“宋祭酒,此乃您上个月亲自呈递上来的奏折。在这份奏折当中,您明明清清楚楚地写道,这些新学科‘于国于民皆有莫大的裨益’。可现在,您怎么能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先前所说的话呢?您如此反复无常,到底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心思呢?”
一时间,整个场面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宋祭酒呆呆地望着那份奏折,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嘴巴张了几张,却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此刻的他,就如同一只被当场抓住现行的窃贼,满脸羞愧与惶恐之色。
与此同时,围观众多的学子们也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他们原本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宋祭酒满怀敬意,可如今看到他这般前后矛盾的言行举止,心中不禁涌起了一丝疑虑和不满。众人看向宋祭酒的目光不再像以往那般充满敬仰之情,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深的怀疑和毫不掩饰的鄙夷之意。
朱标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凝视着眼前的这一幕场景,心中不由自主地暗自叹息了一声。只见他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后,才缓缓地张开嘴唇,轻声说道:“诸位。。。。。。”
此时的朱标慢慢地将视线从众人身上扫过,那张年轻的面庞之上此刻却满满当当地写着迷茫和不解之色。他深知,如果采取强硬镇压的手段来对待这些学子们对于新学所产生的抵触情绪,那么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消除他们内心的抗拒心理,反而有可能使得这种情绪愈发强烈起来。所以,此时此刻的他更需要做的,便是如同那春日里轻柔的微风一般,用一种温暖而又平和的方式去慢慢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逐渐接受并理解这门新兴的学问。
“诸位,”朱标的语调刻意放得十分缓慢且柔和,仿佛一阵清风吹拂而过那般令人感到舒适宜人,“孤心里非常清楚,大家对于这全新的学科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顾虑之处。你们担忧它会偏离我们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正道,甚至害怕它会误导我们的后代子孙。但是,孤在这里想要问一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当真深入地了解过这所谓的新学科吗?你们是否曾经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翻阅过孤呈递给你们的那些相关书籍呢?还有,你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去好好思索一番,如今的大明朝,难道仅仅依靠传统的四书五经就足够了吗?”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过每一张面孔,语气也逐渐变得铿锵有力:“如今,我大明正值开国,百废待兴。我们需要能工巧匠,修建水利,开垦荒地;我们需要精通算术之人,计算赋税,理清账目;我们需要通晓医理之士,治病救人,解除百姓疾苦。这些,难道仅仅靠圣贤之书就能实现吗?孤的本意,是希望你们不仅能饱读诗书,更要能经世致用,成为我大明的栋梁之才!”
说完,朱标转身,步伐沉稳地走进国子监的办公房,只留下一片寂静。
朱标需要时间,也给这些学子们时间去思考。房间内,朱标摊开一张张学子们的名册,仔细研究着他们的背景。谁是家境贫寒,急于出人头地?谁是满腹经纶,却又固执守旧?谁又只是被煽动,盲目跟风?
朱标要对症下药,逐个击破。他提笔,在名册上勾勾画画,时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房间里静的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气氛紧张而凝重,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朱标拟定了一份详细的名单,将学子们分门别类。他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家境贫寒的学子,承诺提供更好的学习资源,让他们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对满腹经纶的学子,则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让他们明白新学科的价值;对于被煽动的学子,则要恩威并施,让他们明白事理。
经过一系列缜密周详的安排与筹划之后,朱标怀着满心期待,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再一次踏入了国子监那庄重肃穆的前院。他身后紧跟着几名侍从,手中捧着厚厚的名册,上面详细记录着众多学子的信息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