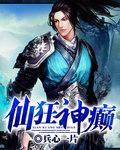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大齐是哪 > 第21章 朝堂风云起波澜义士安危系君怀(第2页)
第21章 朝堂风云起波澜义士安危系君怀(第2页)
“附议!”
“臣等附议!”
老臣的话音刚落,朝堂上立刻响起了一片附和之声,如潮水般汹涌澎湃,气势汹汹,这声音如同汹涌的海浪,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的耳膜,仿佛是一群咆哮着的野兽在怒吼。
那些附和的大臣们,有的伸长了脖子,如同待宰的鹅,有的挥舞着手臂,像是在向皇帝展示他们的决心,好似一群摇旗呐喊的士兵。
他们在附和时,眼睛不时地看向那位弹劾的老臣,似乎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
李启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他能感觉到这股汹涌的反对声中,似乎夹杂着某些其他的意味。
他心里想着,这些人如此急切地弹劾义士军,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朝廷清明和百姓安宁吗?
还是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像在迷雾中探寻真相,却只看到重重幻影。
他的眼神在群臣中穿梭,试图从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中找到答案。
“荒谬!”李启猛地一拍龙椅,发出一声巨响,震得整个大殿都为之一颤,这震动从脚底传上来,连龙椅的扶手都在微微颤抖,群臣中胆小者被吓得浑身一抖,如同受惊的兔子。
他站起身来,双腿用力站直,如同扎入大地的桩子,眼神锐利如刀,那目光似要穿透群臣的灵魂,宛如炽热的火焰要将一切虚伪焚烧殆尽。
他的目光首先扫过那些附和弹劾的大臣,眼神中带着愤怒和不屑,“朕看诸位是老眼昏花了,义士军保家卫国,驱逐贼寇,功勋卓着,你们竟视而不见?他们私设营地,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边境安危,欺压百姓?是真是假,你们又何曾亲自去查证?就凭几句道听途说,便要给他们定罪?”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震得一些心虚的大臣耳朵嗡嗡作响,那声音仿佛要冲破他们的脑袋,好似一阵狂风要卷走他们仅存的理智。
他在心中暗暗恼怒,这群臣平日里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如今却为了不知何事,便要对有功的义士军下手,若不是他平日里对朝堂局势有所把控,今日恐怕义士军就要蒙冤。
他深知朝堂势力错综复杂,这背后必然有着更深的阴谋,他必须要保护义士军,不仅仅是为了公正,更是为了大齐的安稳,犹如一位舵手必须保护船只免受暗礁的威胁。
他环视四周,目光从每一个大臣的脸上扫过,看到那些心虚躲闪的眼神,他的失望更甚,那失望就像冰冷的雨水浇灭心中的热火。
在环视的过程中,他与几位忠诚的大臣有短暂的眼神交流,那眼神中传递着信任与欣慰。
语气中带着一丝失望:“朕以为,诸位皆是饱读诗书,明辨是非之人,没想到,竟是如此鼠目寸光,人云亦云!若朝廷皆是这等庸碌之辈,大齐的未来,又将如何?”
群臣被李启的话语震慑得说不出话来,他们面面相觑,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汗珠顺着脸颊滑落,痒痒的却不敢伸手去擦,就像被施了定身咒的木偶。
整个朝堂鸦雀无声,只能听到微弱的呼吸声,这呼吸声像是风箱在轻轻拉动,又似遥远的风声在耳边轻轻呜咽。
此时,场景仿佛从激烈的朝堂纷争转换到了一种无声的僵持之中,就像从汹涌的海浪瞬间平静成了一潭死水。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尘埃在光线中飞舞,似乎也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凝固了。
李启紧紧地盯着前方,目光如炬,如同一只正在觅食的雄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屑,仿佛是在嘲笑群臣的愚蠢与短视。
“陛下,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张肃忽然开口说道,声音低沉而有力,在寂静的朝堂上显得格外清晰,这声音仿佛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宛如在死寂的黑夜中点亮的一盏明灯。
张肃在说话之前,先是恭敬地向李启行了一礼,
他身着一件青灰色的官服,官服上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只有简单的纹理,显示出他的低调与务实。
他面容清瘦,目光坚定而诚挚,给人一种刚正不阿的感觉。
然后微微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他早就看不惯这些大臣的行径,此时他深吸一口气,心中想着绝不能让义士军蒙冤,那决心如同磐石般坚定,然后向前一步,脚步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像是在地上扎根,如同大树扎根土壤,拱手道:“陛下,义士军虽未受朝廷正式册封,却屡次为大齐平定边患,抵御外敌。去年北疆蛮族入侵,烧杀抢掠,正是义士军拼死抵抗,才保我大齐边境百姓安居乐业。臣以为,义士军非但无过,反而有功。”他顿了顿,声音洪亮,这洪亮的声音在大殿里回响,犹如洪钟大吕敲响,“弹劾义士军者,不是昏庸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他在心里暗暗期待着皇帝能够看清真相,不要被这些奸臣所蒙蔽,仿佛在黑暗中渴望着光明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