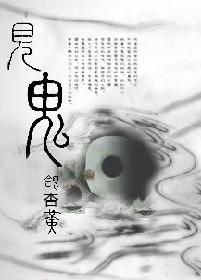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仙居烟雨苑 > 第219章 没用的样(第1页)
第219章 没用的样(第1页)
叶苑苨坚持道:
“如今,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他孤身一人在那绝境之中。不管吃什么苦,我都要陪着他才是。”
曾末语重心长地道:“叶小姐,你且听劝,那地儿万万去不得!那里乃是犯人受刑之所,绝非平常人能够生活之处!”
“更何况你一介弱质女流,那流放之地鱼龙混杂、险恶丛生,你若去了,无异于羊入虎口!”
叶公敷回想起,此前为了让叶公敷能平安抵达流放地,苏云亦四处奔走打点关系,暗中不知费了多少心力。
如此,叶公敷才未在路途遭官爷为难、毒打,全须全尾地到了流放地。
但四个多月的行程,每日赶路,风餐露宿,病痛不时袭来,无医无药,叶公敷也几乎被磨得不成人形。
如今,虽有安排的人暗中照拂,可每日繁重的开荒劳作,依旧让叶公敷的日子过得极为艰辛。
叶苑苨怎会不知其中艰辛,她眼色平静地道:“镇将大人不必再劝我,我心意已决,还望镇将大人应允。”
正是因为那地艰辛,她才要去照应。
否则,父亲若不幸客死在异乡,她作为女儿,连为父亲收尸尽孝的机会都没有。
曾末无奈地看了看叶苑苨,重重叹了一口气,“你容我想想。”
叶苑苨点头,随即告辞离去。
待她一走,苏云亦从侧间闪出,第一句话便是:“绝不可让她去。”
贺家正愁没机会对她动手,她只要一上路,便性命难保。
曾末摸着胸口,坐回椅子,有些烦躁地道:“本官知晓。”
为了苏云亦,他人生第一次办了冤假错案,便被叶家小姐洞悉、质问,幸而他唇舌厉害,这才躲了过去。
但此刻,他内心却备受折磨。
他摇头叹息:
“哎,贺家实在是欺人太甚,把叶家小姐逼到这般境地!本官看着都心有不忍!”
苏云亦闻言,缓缓垂下眼眸,心中蔓延起痛楚与焦虑。
暗暗咬了牙,厉了眸色。
他的谋划得再快些,如此才能早日让叶公敷脱离流放之刑,重回安稳生活。
歇了苑苑跟去的心思。
——————————
洪县西郊山脚。
深非也与康逍墨打累了,二人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边,呼哧呼哧地喘气。
两人脸上都挂了彩,鼻青脸肿的模样狼狈至极。
相较之下,康逍墨脸上更是红一道紫一道,活像开了个染坊。
他小心撑起被揍得四处像开裂般的身子,龇牙咧嘴地摸了摸唇角的伤口。
丝丝凉气从齿缝间倒吸而出,五官都疼得皱成一团。
“妈的,真够狠的。”他嘀咕着,瞪了深非也一眼。
却瞥见深非也把他揍了,却仍垂着眼角,一副丧气模样,像丢了魂一般,没精打采。
瞧着,眼眶红红的,莫不是还想要哭?
康逍墨不禁觉着好笑,冷嗤一声——却不小心扯到嘴角伤口,打了个哆嗦:
“瞧你那没用的样,至于这么一蹶不振吗?一个叶丫头而已,至于把你打击成这样?”
深非也闻言,缓缓背过身去,继续沉浸在伤感中。
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脸旁尘土,画起了圈圈。
苑苑说什么了?她说,她不喜欢他。她还说,他做得再多,她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这些话多伤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