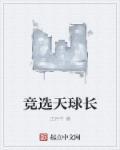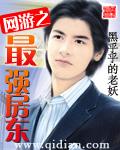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料青山略输我峥嵘下一句 > 第12章(第2页)
第12章(第2页)
百科介绍、记者访谈、纪录片等等形式的相关内容一条条弹出,她略略浏览了一下,便点开了一个纪录片。
熟悉的纪录片式的配音缓缓讲述安山和挑山工的历史,讲述挑山工们的生活,以及游客们对于挑山工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真的挺伟大的,真的,这么辛苦。”游客甲赞赏道。
“其实我不太理解,二十一世纪了,怎么还会存在这样的职业。”游客乙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当问到对于挑山工的将来有什么看法时,一个被采访的小女孩糯糯地说:“希望他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孩子也许不懂阿哥们的辛苦,但孩子却希望他们快乐。
“可爱的小孩儿是真的可以很可爱啊!”沈青边看边感慨。
《小王子》中写道——“每个大人曾经都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沈青回忆自己小时候,她在怀疑自己那时有没有这么可爱。她小时候,也会想要陌生人们每天开开心心吗?
想要陌生人开开心心,也许是因为自己开开心心,因此对看起来不怎么开心的人下意识地同情、怜悯。
可《巴黎圣母院》不是说,小孩子们,“在这种年纪是没有怜悯心的”吗?
“怜悯”作为一种情感,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呢?
想着想着,思路已经飘远了,播放着的纪录片倒成了此时此刻的背景音乐。
当然,思路的开阔带来的是突现的灵感。
放完纪录片,她立马打开码字软件,用一种独特的口吻描写了这几日所观察到的挑山工阿哥们的生活。
文章站在一个生活在安山山脚的十岁小孩的视角,以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身边的挑山工们。
统共十篇日记,四千多字的文章大功告成。
码字软件提醒她,她的小时速度突破了记录,她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写完了这些文字。
到底是艺术源于生活,描写自己深有体会的事,写起文字来便是文思如泉涌。
哪像以前,为了故弄玄虚时的文字,真是一句一顿,卡文卡到奔溃。
写完后,她仔细查验了错别字和病句,又看着文章发呆。
写是写完了,可然后呢?
要发表在网络上吗?
万一发上去,又被网上的人骂了呢?
如今她在网络上的口碑真是不容乐观,确实很有可能被骂。
但是不发表呢?
去投稿给杂志社或者报纸吗?
还是说就让它沉淀在电脑里吗?
文字的使命是被人阅读,即使是被自己阅读。
沈青找了个折中的办法:她找出了自己多年未用的号“晴莘”,改头换面发表了这篇新鲜出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