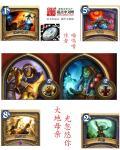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西峰一品上卿 > 第一百八十七章 问君西游何时还(第2页)
第一百八十七章 问君西游何时还(第2页)
这是江河川的原话,在他年近半百的时候,才向人吐露了这个秘密。
他一直说自己是孤儿,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但其实都是骗人的。
他读书不行,记性不错,尤其是幼年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
七岁之前,他都是跟着母亲过的,在扬州的一家妓院里。
他的出生是他母亲的灾难,因为连她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于是她对他动辄打骂,人前人后都不愿意说他是自己生的,怕耽误她的生意。
他睡觉的地方,是他母亲的衣橱,他在那充满艳俗脂粉味的橱子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他不敢出声,无论听见了什么都不能出来……
他蜷在衣柜中被迫听着他母亲房中的闹声,那是他这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但他这辈子最大的噩梦,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
那晚屋子里没有什么声响,一切平静得出奇,那晚他的母亲把所有客人都拒之门外,整个晚上都没有点灯,甚至忘了他的存在,只无声无息地坐在房中。
那是一年中秋夜,她打扮得很好看,比往常鲜艳很多,好像是为见什么人似的,几乎穿戴上了她最好的行头。
可她就这样干坐了一夜,枯等了一夜。
夜里他听到她说话:“出来,到床上睡去吧。”
他迷迷糊糊地出了衣橱,爬上了床,在柔软的被窝里睡了第一个安稳觉。
醒来后,他看见,他的母亲直挺挺地吊在房梁上,僵硬的身体摇摆飘晃。
她死了。
这么多年来,没有谁向他解释过,她为什么会死?
只是有很多人告诉他,人终有一死。
包括那个把他从青楼带走的男子。
在他母亲死了一个月之后才出现,把他带出妓院后的柴房,在满院青楼女子的冷眼中离开那个地方……
老鸨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连妓女都不屑多看那人一眼。
这是江河川这辈子见过的最狼狈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了。
他不敢问他是不是自己的生父,那人让他叫爹,他就叫了。
那个人名字叫江寒山,是个做了一辈子状元梦的穷书生,十六岁就参加乡试考上了秀才,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五次到长安赶考,每次都落榜,耗光了微薄的家产。
接走江河川之前,他刚第五次从长安回到扬州,他什么也没有了,功名无望,穷困潦倒。然后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放弃了科考,但他让自己的状元梦在他儿子身上延续。
江河川与江寒山共同过活的十五年里,他基本上只做了三件事,读书、忍受贫寒,以及听江寒山一遍遍说着遥遥长安城的繁华盛景。
长安,长安,总是长安。
所以,他不爱江南,他不想在江南老,他跟许多出生在江南的年轻人一样,寒窗苦读多年,一心憧憬着皇城帝都。
长安城里人先老。
这句词二十五年后他才感同身受,这个时候他真的老了,不再是渭水河畔那个迷茫徘徊的清寒书生。
他和二十五年前一样,不愿意承认,他想念江南。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此生还能回去吗?回去又怎样呢?
不,回不去了。
……
二十五年前的上元节前夕,他孤身一人,他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他只能确定一样事情——长安,他来了,就不会再离开。
长安城里唯一不用银子就能获得的就是,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