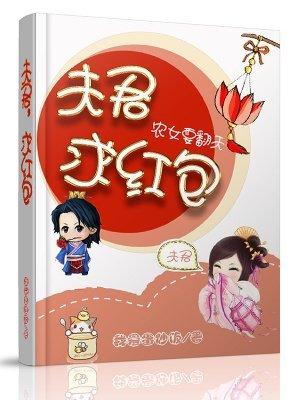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山里汉的小农妻最后女主嫁谁了 > 第108章 忠诚所致金石为开(第2页)
第108章 忠诚所致金石为开(第2页)
沈若兰抬起头,说,“是我今年在老家那边儿开出来的地的收成账!”
今年沈若兰在凤凰村那边儿一共开出了六百多亩的山地,只是因为是第一年才开始种,土不够肥沃,而且山地的位置偏高,存不住水,今年雨水又不足,所以收成很不好,只有相对于地势洼一点儿的地才有点儿收成,地势高的地都瞎了,根本就没有收成,开出六百亩地,收成还不如好地一百亩的收成多,几乎折本儿了。
淳于珟看到她闷闷不乐的,安慰说:“折本就折本吧,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咱们王府里也不缺这几两银子几斗米的,何必为这点儿事儿不开心呢?”
沈若兰说,“我并不是为了少赚几两银子不高兴,而是因为粮食打的少有点儿失望,六百亩地就打了不到一百亩地的粮食,跟我预想的差的太远了。看来,我还得好好研究研究,为啥收成这么差?怎么才能把粮食的产量提高上去。”
淳于珟见她差蹙着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拿开她手中的账本,揽着她的腰肢,说,“这些地本来就不好,不要也罢,咱们王府有十几个庄子几千亩地呢,你要是喜欢看收成好的,就看咱们庄子里的账本吧,包你满意。”
一边说着,一边顺着沈若兰身上传出来的淡淡的香味儿凑过来,闻了闻她的脸颊,只觉得香喷喷的。
今儿孩子百天,有客人来道喜,沈若兰就略施粉黛,擦了点香粉,又穿戴了几件华贵的衣裳,打扮得跟下凡的仙女似的。
淳于珟在席上喝了不少酒,本来就心猿意马的,如今又坐在媳妇的身边,看着她的盛世美颜,更加觉得难以把持了。
因为她年幼产子,对身子的损伤很大,太医说过叫她百日后方可行房事,所以这几个月来,他一直扳着指头算日子呢,就等着满一百天好大干一场了。
如今已经满一百天了,她身子也恢复好了,应该可以了吧……
沈若兰的思想却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她还在想着今年的收成,兀自说,“咱们庄子的账本儿我当然要看,但是我自己开的这些地我也要经管,那些山地的土质我都看过了,都是正宗的黄土地,适于庄家生长的,虽不如黑土地好,但是也不至于收成这么差,我在好好想想,找找原因,争取明年把收成搞上去!”
这时,喜宝儿吭吭叽叽的哭起来,应该是到喂奶的时间了。
素素提醒了沈若兰一声,沈若兰忙收回思绪,不去在想那些庄稼收成的事儿了,解开身上的褙子,把喜宝抱起来,开始哺育。
喜宝闻到娘身上熟悉的香味儿,立刻就不吭叽了,在沈若兰的怀里拱了一会儿,找到了奶头,叼在嘴里滋滋滋的裹了起来。
淳于珟本来就心猿意马的,又看到了这副香艳的画面,终于憋不住了,一只大手悄悄的伸过来,在沈若兰的身上游移着。
喜宝虽然只叼着一直奶,但小爪爪却紧紧的护着另一个呢,当父王的大爪子侵犯到他的领地,喜宝立刻不满的哼哼起来,小爪爪抓着父王的一根手指头,想把它驱离自己的领地。
然而,父王的那只大爪子跟一只大章鱼似的,紧紧的握住了他的饭碗,根本赶不走。
喜宝生气了,吐出奶头抗议的哭起来,“哇……”
小家伙脾气大得很,一哭眼泪都出来了,小鼻子头也哭得红彤彤的,这把沈若兰给心疼的。
开始时,她看他跟自己不正经并没有理会,但是这会子看到他把儿子都给惹哭了,就不由分说的站在了儿子的一边,抬手就去掰那只吸盘似的‘大章鱼’,“你看你,孩子好好的吃奶呢,都叫你给弄哭了!”
“兰儿……”
淳于珟喘着粗气叫了一声,“咱们都好久没有那个了,太医说一百天就可以了,今天正好是一百天……”说着又往前凑了凑,一口咬住了她的耳垂。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沈若兰被他一嘬,打了个冷战,低斥说:“你干嘛啊,现在是大白天呢,等晚上再说不行吗?”
淳于珟看着媳妇低头娇嗔的样子,心更痒痒了,无耻的说,“就是百天才刺激呢,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再说,这都如箭在弦了,哪儿还等得到王晚上啊,不信你摸摸!”
沈若兰两只手都抱孩子呢,哪空的出来去摸他呀?再说就算空得出来,她也不好意思真去摸啊!
淳于珟见沈若兰红着脸,一副娇羞的样子,越发的心痒难耐了,干脆一手捏着喜宝的饭碗,一手去解沈若兰的裙子。
沈若兰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并不像古代女人那么放不开,且她正值青春年华,体能旺盛,对男女之事也喜欢的很,所以被淳于珟医疗博,就也娇喘吁吁的上了港了。
眼下喜宝还吃着奶,俩人虽然都是疼孩子惯孩子的,虽然都已经是迫不及待了,但是也都舍不得就让孩子吃到一半儿就停下,于是就只管先让那小东西吃着,他们两个先忍着。
淳于珟把沈若兰抱在腿上,让她感受着自己现在的变化,沈若兰促狭的扭了扭身子,轻微的摩擦就让他一阵倒吸冷气,差点儿爆炸。
“你就不能消停点儿嘛,连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他长臂一紧,将她固定住了,不许她在撩拨他了。
沈若兰仗着有子傍身,他不敢把自己怎样看,被固定住后,忽然一回头,呲着细密洁白的小牙,在他的耳朵上咬了一下。
这个举动,一下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本来就是在极力的隐忍着的,要不是看在可爱的大儿子的份儿上,早就把她就地正法了,可是她不知死活,非要‘作死’,终于把他给引燃爆炸了。
于是……
沈若兰低头看着自己突然露出来的两条纤纤玉腿,差点儿被羞死,真没想到他竟能这么不要脸。
记得刚认识他时,他是何等的冷傲矜贵,霸气横生,目空一切,睨视天下啊,可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