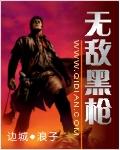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 第13章(第2页)
第13章(第2页)
其实只需要下一道圣旨,何必特意将他召回上京呢?
罢了,大人们的想法,还是不要过度揣摩的好。
他回想起朝堂中站在最前排的那些人,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下了朝,谁不是个动辄天下惊的角色?
那一身朱紫朝服,寻常百姓一年的开销,只怕也换不来半只袖子。
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就是这样大,隔着天与海。
话说回来……那位张爷不知近况如何了。
身体是否康健,武艺是否生疏,家中是否……添丁?
否则为何忙碌到,一封信也无暇寄来。
75
古伯倒是书信未断,言说书院无存,再无挂碍,如今回了老家,当回了古夫子。
故而不巧,他也难知张车前的近况。
思及此,燕一真悄悄叹了口气。
书信有去无回,他便不再托人带去,几年下来,不觉攒了厚厚一匣。
放床头怕磕了碰了,放桌案怕落灰脏了,放斗橱又怕遭了虫害。最后干脆压在箱底,藏在冬日的裘披里。
其实信中全是芝麻小事,肉价见长、自创腌制新法、邻居总爱半夜吵架、给新建堤坝题的贺诗竟受到全城百姓交口称赞,诸如此类。
既无通敌之嫌,又无叛国之疑。为什么要藏呢,并不会有人来偷来抢。
只是他也想不明白。
作者有话要说:
70章之前修改了,然后不小心发错了原来的,所以这次一起补上。
第16章【76-80】天长之秘
76
天长开县已久,古迹众多。燕一真一路行来,目不暇接,惊叹连连。
更遑论此地佛缘浓厚,人人谦恭有礼。护国寺、宝林寺庄严肃穆,路不拾遗,一派天下大同的气象。
圣旨中不是说天长……荒山野岭,地处偏僻,时有流寇作犯,前任知县造反途中染病而死,故而民不聊生么?
难道有官员谎报民情不成?
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来之,则安之。
燕一真安下心,寻到府衙前,整整衣摆,向前来迎接的门童亮出赴任告身。
77
府衙窗明几净,布置素雅,屋中书墨馨香,加之县中情形,足见前任知县为人。
然而衙人眼中俱是悲愤,似有天大冤情。可每个见到他,却都欲言又止。
这是怎么回事?
回想起沿途种种流言,燕一真心里逐渐有了猜测。
行至偏房,四下无人,他拉住带路的老管事,低声问道:&ldo;敢问商知县是何时何地、因何事犯何病而去?&rdo;
老管事一震,缓缓回身,只见他眼眶通红,喉咙几度哽咽,最后扑通跪下:&ldo;老奴该死!小子们该死!&rdo;
&ldo;为何该死?&rdo;
&ldo;回大人的话,这本不关大人的事,可,可大家伙儿不服啊,商大人,商大人是被人害死的!&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