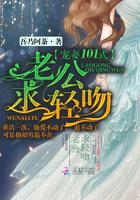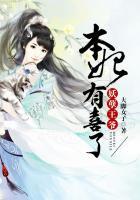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多少页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在远离冲突的世界另一端,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对这场爆发于欧洲的战争,反应之积极丝毫不亚于任何英国人。澳大利亚当时的在野党工党领袖安德鲁&iddot;费希尔,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承诺,澳大利亚将支持英国作战&ldo;直至耗尽最后一兵一卒、一分一厘&rdo;。1914年8月初,澳大利亚联邦动员了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新西兰亦召集了新西兰远征军。他们共同组建的军队被人称作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团,简称澳新军团。
早在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曾派遣军队支援英军。然而,那次异国作战的经历丝毫未能帮助澳新士兵直面一战的血雨腥风。布尔战争时,共有16万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派往南非,只有251人阵亡;更多(总共也只有267人)死于疾病等非战斗减员。新西兰军的死伤率也基本相同:6500名战士中只有70人死于战斗,23人死于意外,另有133人死于疾病。布尔战争的经历使两国人民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对未来的探险和异国之旅充满期待,并笃定地认为最后都能衣锦还乡。[24]
澳新军团包括骑兵队与步兵团,大部分骑兵队的志愿兵都来自乡村,骑着自家马匹前来报到‐一战中约使用了1600多万匹马。这些士兵可以选择登记自家马匹入伍,一旦马匹通过检验便能得到30镑报酬。此后,这匹马就为军队所有,它们被烙上政府标识,其中不少印在马蹄上。一匹被骑兵称为&ldo;替补&rdo;(reount)的战马必须达到严格的标准:阉马或母马,年龄在4到7岁之间,肌肉发达,不高于152掌宽,状态良好,且不惧战火。澳大利亚一种名叫&ldo;新南威尔士&rdo;的马是纯种马与挽车马的混血后代,符合上述标准。[25]
新西兰远征军士兵来自全国各地,背景也是五花八门。他们之中有农民、手艺工匠、牧羊人、丛林居民、文职人员、教师、股票经纪人以及银行家等,不胜枚举。他们参军是因为朋友都来了。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战争不过是一场大冒险;而另一些人参战却是出于对英国的热爱。他们之中没人了解未来即将面临的战斗是多么凶险,在经过6周的训练后便纷纷准备启程。特雷沃&iddot;霍尔姆登,一位来自奥克兰的年轻律师,记得他与同伴从位于一树山(onetreehill)的训练营行军至港口等待渡船的情形:大批奥克兰人都来目送我们离去。尽管多数看客是高兴他们终于可以摆脱眼中的一些混混了,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天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对行军非常自豪,也乐在其中。整个过程当然很戏剧性也很令人斗志昂扬,一路上乐队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我们……从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而来,登上了船,穿过女皇码头的那道铁门,驶向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彼岸。[26]
由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人口较少,因此参战的军队规模也有限。1914年时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约500万,新西兰则只有100万。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子,或21至40岁的新西兰男子,身高5英尺6英寸及以上,体格健硕者方有资格参军。截至8月,澳大利亚已招募到19500人(17400名步兵,2100名骑兵),由将近900名军官统领。新西兰远征军共有约8600名士兵与3800多匹马,除了1400人被派去占领德属萨摩亚,其余的士兵都在3周之内整装待发。[27]
由于报道称有德国海上部队在南太平洋一带活动,运兵船只受其影响也延误了到港时间。虽然志愿兵在9月底就已训练完毕,但10艘运兵船直到10月16日才从惠灵顿起航,中途由一艘日本战船与两艘英国舰船护送。弗兰克&iddot;霍尔姆登与1500人及600匹战马同在&ldo;瓦伊马纳&rdo;号船上,&ldo;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rdo;。他们先驶往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汇合,11月1日再从澳大利亚西南港口城市荷巴特出发,当时目的地尚不明确。奥斯曼帝国在11月2日才加入一战,而那时澳新军团已经出发了。这些澳新士兵并非驶往英国,而是将在埃及登陆,投入中东战场。
当英法两国动员自己的帝国投入欧洲战争时,他们也不得不细细考量其治下的穆斯林臣民是否忠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公民待遇,早已怨声载道。另一边,几十年来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后者愈发效忠于有全球穆斯林哈里发之称的奥斯曼苏丹。而在埃及,英国长达30年的占领已促使其境内爆发了以独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是之前他们的行动都被挫败了。鉴于上述情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英属印度和北非的殖民地政策已让当地穆斯林渐行渐远,现在可能转投英法的敌人‐德国的怀抱,通过后者的胜利获取自身独立。[28]
对于处在关键时刻的大英帝国而言,埃及极为重要。苏伊士运河是连通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要道。位于埃及的军事基地在供皇家军队训练的同时,也充当着中东军事行动的据点。倘若埃及民族主义者利用欧洲战乱,或虔诚的穆斯林响应圣战,将会给英国的战争大局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战火于1914年8月在欧洲点燃之时,埃及政府正值夏季休会,时任埃及总督的阿拔斯&iddot;希里米二世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休假,立法议会也处于休会状态。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机,首相侯赛因&iddot;鲁西迪帕夏不得不在未请示总督的情况下当机立断。8月5日,英国对鲁西迪帕夏施压,迫使其签订了保证埃及向同盟国宣战的文件。然而此举并未能确保埃及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相反,消息一经传开,埃及人民便义愤填膺。据一位当时在埃及工作的英国官员回忆:&ldo;各个阶层的埃及人都对殖民者(例如英国)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现在这种不信任升级成了‐即使他们仍保持沉默‐赤裸裸的仇恨。埃及本就不愿,也不齿其与英国有关联,它现在更让埃及陷入毫无缘由也毫无目的的斗争。&rdo;[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