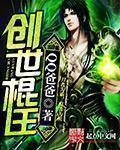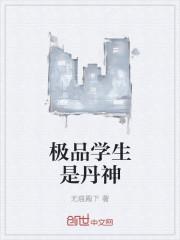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名将之死连环画 > 第110章(第1页)
第110章(第1页)
可惜当时李广不在军中。
这是汉武帝封赏最为大方的一次。从那以后,对卫青的标准日渐严格。当然,卫青食邑已多,按《史记》记载共有一万六千七百户,《汉书》更有二万二百户之多。这个数量相当惊人,要知道汉初整个长沙国也不过两万五千户。
读过《史记》与《汉书》中的有关传记,李广难封的谜团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令人疑惑。仔细读史,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所谓&ldo;李广难封&rdo;的冤屈,真是千古奇冤,不白之冤。这根本就是个文化骗局。或者说得更明白点,是历代失意文人不断附会后形成的文化形象,与真实的李广完全是两码事。
从头到尾,汉武帝对李广都是赏识的,至少从无恶感。开始让他做长乐宫卫尉,后来又让出任郎中令。这两个官职都是天子近臣,在九卿位次中分列第二和第三,职位要害。其中郎中令的实权尤其大,几乎就是所谓的&ldo;大内总管&rdo;。若非汉武帝绝对信赖,断无可能出任此职。现代官场可能会有这样的领导,故意将恶心的人留在身边,目的是看死他,恶心他。当然这是双输。领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生杀予夺大权,最多不让人家干实职中层,工资你都停不掉。汉武帝难道还需要这样互相恶心而隐忍不发吗?
从后人的安排也能看出汉武帝对李广的同情或曰好感。李敢跟随霍去病出击漠北,夺得左贤王旗鼓,回来后赐爵关内侯,食邑两百户,接替李广担任郎中令。如果汉武帝讨厌李广,何必如此?
汉武帝赏识李广非常正常,这是个可爱的将军。缺点和优点同样鲜明而且真实。他精于骑射,有勇有谋,胆大心细,体恤士卒,忠心卫国,都是优点;心胸狭窄、气量不够,则是缺点;至于渴望封侯,乃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算是中性。
李广的顶头上司卫青,更不需要故意遮挡他的阳光。无此必要不说,更重要的是,这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卫青此人在官场跟沙场征战一样内行,懂得自保。素来老成持重,低调宽厚。他不杀苏建立威,为将士请功;李敢将父亲之死的账记到他头上,将他击伤,他时为大将军,权倾朝野,可是却没有声张。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度。李广恐怕做不到,公子哥儿出身的霍去病更做不到:后来李敢陪同皇帝到甘泉宫狩猎,霍去病悄悄将他射死,以为舅父雪耻。当时霍去病正走红,所以汉武帝没有加罪,反倒寻出一个类似黑色幽默的理由,为之开脱:&ldo;鹿触杀之&rdo;。
上林苑的鹿果然不凡,竟然能用角抵死夺得左贤王旗鼓的勇士。
既然皇帝和顶头上司都无为难之意,那干吗非要把他从前锋线调开?很简单,此间只有公心而无私怨‐‐在卫青那里,公私相得益彰,但有私无怨。本来汉武帝就不想让李广出征。地球人都知道他&ldo;数奇&rdo;,运气不好,更何况年事已高;可是转念一想他鞍前马后为自己效力几十年,不觉心生恻隐,又给了他机会。
就是这个恻隐,好心办了坏事。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的话。
在皇帝与大将军眼里,战役胜败跟个人荣辱之间,毫无比例可言。任何人到了那个位置,都得做出同样的安排。否则就是缺乏职业素养。如果我是卫青,即便没有上意,也不会让李广打前锋。当时的人比现在更相信未知的神秘力量,更相信命运。哪怕他只是千万分之一的&ldo;数奇&rdo;可能性,我也得照完全不可靠来考虑。否则我就不是个合格的元帅。那时李广的名声全部成为拖累:他名声越高,我越不能用。道理很简单。此人名气那么大,却一辈子没立功,谁能相信?我大可不必在他身上为自己的眼力押宝。否则一旦押错,数万将士就将血染黄沙。那一仗汉军的代价也确实极度高昂,从民间征用的十四万匹马,最终只回来三万匹,不足零头。军士们的伤亡,可以想见。
人们常说,司马迁把李广的传记写得很漂亮,但对卫青与霍去病却是另眼相看,他们的传记简直&ldo;一钱不值&rdo;,因为司马迁之所以受那种屈辱的刑罚,缘起于他为李广打了败仗的孙子李陵讲情,惹得汉武帝雷霆震怒;李广劳苦功高不得封,而卫、霍二将起自裙带关系,云云。
单从行文而言,李广的传记确实精彩动人,堪为绝唱,而卫、霍的传记则是干巴巴的流水账。账目精确到个位:二千零二十八。然而卫青起初是汉武帝的小舅子、霍去病起初是其内侄儿,这不假;但到后来,二人的身份都已发生质变:前者是安邦定国的大将军,后者是深入虎穴的汉军魂。还是让数字说话吧:卫青七次出击匈奴,斩首五万余级;霍去病六击匈奴,斩首超过十一万。况且起初得官不正,并不是他们的责任。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此二人确有将略,又怎么不能重用?
第14节:百战将军难封侯(13)
只有棒槌才读不出司马迁对李广的深切同情。问题在于这种同情并未偏离史家的根本原则。作者本人,当然应该而且必须要有淋漓充沛的感情,否则就无法成就千古名篇,只能增加故纸堆中的垃圾。无论对李广还是对卫、霍,我认为司马迁的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对李广,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卫、霍,你们有功封侯天经地义,但我保留不喜欢你们的权利。
回到李广身上,&ldo;亡道后期&rdo;是正常现象,并非其无能之表现。如果你去过沙漠就会明白这一点。茫茫沙海四面无边,毫无标志可作参照,迷路本来就是大概率事件,更兼向导逃亡。其实不止李广迷过路,公孙敖也迷过,就连曾经在西域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张骞也未能幸免。而且按照惯例,这个罪过当斩,但不会真斩。有爵位者以爵位顶罪,无爵位者可以钱赎罪。这一点谁都明白。因此卫青派人过去调查时,还带着干粮牛酒,以示慰问。既考虑到了李广身为老将的面子,也算是临时改派任务的歉疚。双方都有面子,李广完全可以借坡下驴,但是他没有。他说得很清楚:已经心灰意冷,不想再受刀笔小吏的羞辱。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李广完全被声名所累。飞将军的美名,捧杀压垮了他。大家都有这种印象,他理应封侯。从文帝开始,这个气泡越吹越大,效应有内外两方面:从内而言,别人说得越多,李广越信以为真,封侯的心理预期越高;就外而言,别人越发相信他确实&ldo;数奇&rdo;。所以汉武帝先是不愿意派他出征,后来又临时调整部署,不让他当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