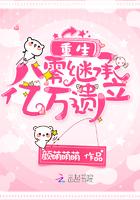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明月东升西落 > 第166章(第1页)
第166章(第1页)
很快,这些谨慎前行的哨探游骑便发现坎川岭一带出现无数后金旗帜,对这个他们本就已经熟悉,再加上辽阳传达的后金情报,很容易辨认出那属于后金镶黄旗的军旗,虽然并未看见有多少人,但这就足够了。这些人几乎是逃命般地返回大营,禀报说,前面驻扎着镶黄旗精锐。
这个消息让姜宏立与乔一奇都大为吃惊,一则镶黄旗是努尔哈赤旗下最精锐的兵马,二来,这刘綎在前,中间却出现大批后金人马,岂不是将二队切断?而刘綎怎么能放敌人到自己的身后?那只有一个结论,便是刘綎已经被敌人包围,凶多吉少。当下朝鲜武官们便达成一致,暂不行进,等够确切消息。那乔一奇主张直接进攻,将敌人吃掉,继续前行与刘綎汇合。这绝对行不通,不论乔一奇如何发怒、摔做桌子,拔刀砍椅子,都不奏效。整整一个下去,这种来自大帐内的争吵都没断过。但,夜色降临,乔一奇也没了办法。一天一夜便在高度戒备中过去了。第二天,敌人仍然没有前来进攻,而军需官禀报,说说是粮食只够全军半日份量,若后队粮草再不接应,全军今晚便要断粮。姜宏立等众人的争吵有持续了一日,还是没有结果,敌人既没有进攻,也没有骚扰,但要命的是,粮草终于断了。当夜除了武官们,只有少部分朝鲜兵马得到吃食,大部分都只能忍着,期待第二日粮队便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也是都帅所说。
第二日上午,乔一奇没有再争论,朝鲜武官们也未再有提议。然而粮食依旧无影无踪,姜宏立等不及了,下令全军返回,不再管辽东这次军事行动。
断粮的队伍走了一日,沿途始终没有遇到运粮队伍。姜宏立下令全军继续前行,若无粮他这都元帅也毫无用处。此时,于承恩出现了。
此人在前天的战斗中摇晃红旗被人盯住,当然,他也是第一个被俘获的军官。这一次,苏翎将其放回,什么也没交代,只在朝鲜大营的不远处将其放下随即飞快隐藏起来。
逃生的于承恩直接进入朝鲜大营,将刘綎所部之事一五一十地全部交代清楚,而姜宏立,在惊诧之余立刻明白,自己这些人,已经全然在苏翎的控制之下。尤其是那于承恩对与苏翎所部的战力的夸张,让这一切更显得危机重重。那刘綎的威名可不是假的,既然他都被干掉,自己能躲的过去么?就算前面没有人拦截,一万多人没有粮草,是走不到宽甸堡的,只怕半路上便被饿死一半,而另一半,将会被冻死。
当苏翎带着数百骑兵列队迎接撤退的朝鲜人时,朝鲜军马已经被饥寒逼的行动无力,根本没有半点抵抗意志。苏翎要做的,便是等着接受朝鲜人的投降,否则,身后的火炮会立即开火。两侧山谷中隐藏的骑兵也会立即包抄两翼,将朝鲜人就地歼灭,甚至有少部分愿意加入的明军士兵,还等着拿几个人头当作报效之礼。
就在刘綎全军覆没的那一段山路上,被饥饿以及寒冷折磨得气力全消的朝鲜兵马逐渐到来,见到整齐列队的铁甲骑兵,于承恩有关苏翎的描述一一得到证实,尤其是那面血红的新月战旗,象一团火一般煎熬这朝鲜士兵。
姜宏立只有一个选择,全军投降。那边乔一奇刚要反对,便被一旁的朝鲜士兵一拥而上捆成一团,而其亲兵家丁一旦反抗则立即被杀,其余的,尽皆被绑了起来。
苏翎眼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观看数不清的战利品,以及成群饥寒交迫的朝鲜士兵。一万多人全部投降,在勉强吃了一顿饭充饥之后,这些善于忍耐的朝鲜士兵被重新规划成十个战俘营,在骑兵大队的带领下,搬运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向群山之中走去。这速度自然是要快上一些,那滞后的粮队,则在更早之前,被数倍于自己的骑兵歼灭,所有粮草全被缴获。
至此,东路军马彻底消失,而苏翎,这位千山堡势力的代表者,将自此走向更广阔的区域,拥有更多的人马,更多的土地,更多的世界。
不过,当其余几路明军的消息传来时,千山堡却面临着另一种危机。
【故事到此时算是过了最初的基本生存阶段,实际上努尔哈赤也是在此时跨越了一道分水岭,接下来,是努尔哈赤扩张的阶段。而本书中的千山堡,也进入与努尔哈赤比肩的过程。】
【本书的写法在起点算不得主流,希望喜欢本书的朋友多多支持苏潜。苏潜将尽力展示一幅最接近真实的架空历史。啰嗦几句,请海涵】
第一卷辽东轶事‐第四卷铁骑夺金
第三十二章何去何从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三月十五日清晨,初战大胜的千山堡如往常一样,在寒气未退的晨风中醒来,早起的人们依照惯例,在弥散着炊烟的巷道中穿行。堡墙上彻夜值守的士兵正在换班,两队排着整齐队列的士兵在发生一声呼喝后,彼此交换位置,换下来的士兵则沿着梯道走下城墙细心的人们发现,那两队士兵中,出现许多陌生面孔,而平时熟悉的那个略带腼腆的年轻人,正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胸前的黑色铠甲上,别着一枚银光闪闪的五星。
这似乎是千山堡内唯一能看出来的变化,但,如那个年轻人一样获得升职的人还有很多,随着自愿加入的降兵数量的增多,千山堡扩充了几乎一倍的编制,这让那些表现出色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身作为精锐的军事技能。

![[陆小凤]花叶藏林](/img/4120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