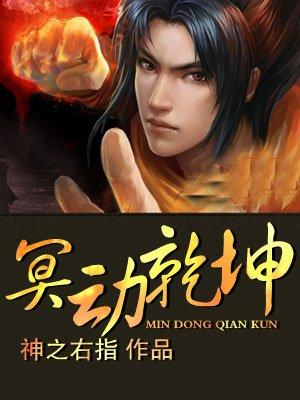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云深不知何处去下一句 > 以身犯险为君还(第4页)
以身犯险为君还(第4页)
子弹虽多,却大多是随意打的,二人动作又快,竟也只有了几处小的擦伤。眼看就要跑出大门,不知是何处发来一枚子弹,生生射入林潇的肩胛骨。
林潇脚下的步子踉跄了一下,亦尔一直被他护在身前,是以看不见他的情形,却也知道他定是受了伤,忙问道:“你怎样?”
“无事!”林潇咬了牙,仍旧护着亦尔往外跑,竟真教他们跑出了司令部的大门。
亦尔一边往后打枪,一边道:“林潇,往前面的巷口跑,车子停在那!”
林潇未曾应答,只顾拉着亦尔跑。那枚子弹想是陷入了骨头当中,疼地他额上直冒冷汗。然而林潇半点也不敢放松,护着亦尔快速往巷子里跑。
终于入了巷子,果见一辆车停在巷中,亦尔把林潇往副座上推,自个上了驾驶座,一脚踩了油门把车往外开去。
追捕的人马亦追到了巷口,亦尔只当没看见他们,油门半点不放松便撞去,众人忙往后退,亦尔借机将车开了出去。
车后追捕的人依然还在,子弹不时打在车厢上,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林潇靠在副座上,一张脸煞白地毫无血色。
亦尔心疼不已,只是这里是黎远山的地盘,她是万万不敢停车给林潇检查伤口的,只好不停地踩着油门把车往城外开。
城门处已加派了不少人手,还设了防拦不许人出城。见到亦尔的车,守城的兵卫连忙要拦,亦尔却半点不曾理会,径往外冲去。所幸那阻挡的只是木栏,亦尔踩足了油门便也冲了过去。
打在车厢上的子弹愈发多了,撞击着发出极大的响声,几乎有种要穿厢而入的感觉。亦尔额上已是一层细细的汗珠,却半点不敢松懈,只顾着顺着路开去。
只要出了南昌便安全了!
车子愈开愈远,车后的枪声逐渐少去。亦尔仍是不敢懈怠,直开出一个多小时,眼看着进了东乡,她方才舒了一口气。
到抚州的地界了!
因为抚州是年世勋的地盘,他们自然是安全的,只是离军部所在的抚州市区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林潇又不知伤势如何,亦尔只得暂且停车检查。
这处是荒野,莫说大夫,便是连人也见不得一个,亦尔无奈,唯有亲自给林潇包扎。一路的颠簸,林潇早已因失血过多而脸色苍白地倒在座上。亦尔把车停好,转去看林潇,他仍穿着黎远山军里的黄斜纹布军服,背后被血染透,显出一大块暗色。
即使第一次杀人也不曾惊惶的亦尔,此刻双手竟颤抖地提不起来。
她再次红了眼眶,蓄了满眼的泪,只不过方才在黎远山面前是做戏,此刻却是真真的伤心难过。她深吸了一口气,颤着手去掀林潇的衣衫。时间久了,那衣服已粘在了林潇的皮肤上,边上又无剪刀,亦尔咬着牙把衣服用力撕开,便听得林潇闷哼一声,伤口涓涓地往外流血。
双眼被泪遮地雾蒙蒙一片,亦尔抬起旗袍的衣袖抹去,低下头仔细查看林潇的伤口。极深的一个枪眼,正在肩胛的位置,看不清子弹的位置。这车上并未备包扎伤口的药物绷带,这血又一时止不住,亦尔想了想,干脆俯下头,以唇舔去伤口不断渗出的血迹。
入口满是腥甜的味道,浓重的血味几乎让她反胃。然而别无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尽快为林潇止住血,亦尔唯有强忍着舔舐血迹。
不知喝下了林潇多少血,亦尔终于感觉到伤口不再往外冒血珠,她抬起头,也顾不上唇角还带着浓重的血色,便慌忙去找能够包扎的东西。
然而什么都没有,身上唯一带的一条手帕方才丢在了黎远山的房里。亦尔四处看了,最后把视线停留在自己身上那件旗袍上。
那旗袍开叉开得极高,露出她一双白希修长的腿。然而亦尔此时顾不得这个,她捏住旗袍的下摆,自开叉的地方用力扯去,许久方才扯裂些许。顺着裂开的口子,亦尔用尽全力一扯,硬生生自旗袍上扯下来一条。亦尔舒出一口气,小心地用那布条缠上林潇的伤口,缠好后,又极为轻柔地将林潇扶到后座,让他趴在后座座位上,以免压着伤口。
做完这些,亦尔回到驾驶座,极为疲惫地把身子靠在座椅上,长长叹了口气。
之前只顾着逃命,安全了又一心惦着林潇的伤口,此刻终于得了片刻空闲,亦尔方才觉得左手的掌心火辣辣地疼起来。她摊开手看去,被火药灼伤的掌心因为自己这一连的动作而血肉模糊,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她望着自己的手掌,一时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事情是不是变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她这样的家世,这般的容貌,不管是当初在国外,还是如今回了国,追求的人从来都不少。可是她素来是自由惯了的人,从不曾对谁用过心。直到几个月前,父亲提出让她嫁人,她才决意找个能让自己动心的结婚便是。
可是,她原想找的,只是个“能让她动心”的人呵!林潇似乎出现地恰是时候,他又正巧让她十八年来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对他“以身相许”。可是,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她竟会这般喜欢他、在乎他,喜欢到可以为他杀人,在乎到可以为他豁出命去!
亦尔回头看一眼林潇,他睡在后座上,略显急促的呼吸已渐渐恢复正常,一丝一丝极为清浅。
她敛下清亮的眸子,轻叹。
罢了,想必是天意罢!那便这样吧,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她摇头,再次踩下油门,控制着方向盘往前路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