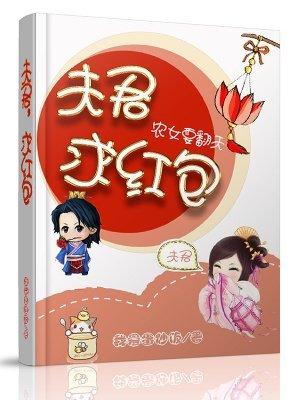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女巫大人万万岁免费观看 > 第一百六十七章 执手承诺(第1页)
第一百六十七章 执手承诺(第1页)
门吱嘎一声开了,里头是通红了双眼的淡薄身影,云瑶缓缓站起身,望着那样的世遗,伸手轻轻的拂着他那清瘦的脸。
“世遗。。”
“云瑶。你说,我们会不会一起,白头到老?”
世遗打着手势。。
“会的,会的,只要世遗不离开云瑶,云瑶就一定会好好的在世遗身边,不离不弃。”
“可是云瑶身边有那个好看的男子。”
云瑶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她知道自己太过自私了,她确认,就在刚才,她内心深处一直被自己忽略掉的感情再次苏醒,这一年来,她根本就没有忘记过云离殇,可她也知道,她再也放不下世遗,这个干净的男子,
“世遗,对不起,离殇,是我的未婚夫。”
世遗抬头,有些迷茫的望着云瑶,那个男人,是云瑶的婚定的人,那,那为什么一年多前,云瑶伤横累累的躺在溪水中几乎奄奄一息,为什么没有来找云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来找云瑶呢?
“世遗,云瑶很在乎你,云瑶想跟世遗一直一直一直白头到老,可是云瑶有很多事情不能抛下,如果云瑶能心狠些,有或者坚定些,一切就都不会这样了,对不起世遗,是云瑶伤害了你,你想要打云瑶,骂云瑶都可以,但是你不要伤害你自己,不要将自己关起来,不然云瑶会很难受很难受,这儿,会很疼。”
拉过世遗的手,放在自己胸口,哪儿是心脏的位置,云瑶有节奏的心跳声,一下两下,世遗能感受的到,那是云瑶的心跳声。
“云瑶,对不起。。”
“傻子,没有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如果非要说对不起,只能说云瑶太多情。只是你们一个个对云瑶来说,都很重要,云瑶不知该怎么是好。”
“云瑶,我突然想听你讲故事了。”
比划着手势,这一年来,云瑶早就知道了他的手势,是想要表达什么。
“为什么?”
世遗摇了摇头,他不想说,那时候,云瑶只是他一个人的,他不想说,那时候云瑶身上就会散发出暖暖的感觉,他不想说,那时候的感觉,就像是他和她,已经是成婚已久的夫妻,坐在草坪上聊着过去,他不想说,那样子的时候,很温馨。
“因为好久没有听了。”
从前没有事情的时候,云瑶总是能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说与他听,而他,也很喜欢听。觉得很实在,毕竟那时候,整个山谷,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云瑶那时候行动不方便,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靠他照顾,那时候的他,是被云瑶依赖的吧?虽然他知道,云瑶有时候会嫌弃他笨手笨脚,嫌弃他做的米粥不好喝。但他知道,那时候,他是被云瑶依赖的。可后来呢?云瑶的伤好了,云瑶发现了绝情殿,第一批绝情殿的人员来到,云瑶开始忙碌,开始脚不沾地,陪他的时间开始越来越少,他忽然觉得,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人,但每当看到云瑶的时候,他的心里,又总是会暖暖的,很舒服很舒服,很安心很安心,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爱情,现在懂了,云瑶的身边,却出现了一个一个更加俊朗优秀的男子,而他,不过是一个连说话都不可能的废物,甚至照顾不好自己,又如何,去照顾云瑶呢?
“那我们就去屋子里说好不好?”
世遗点了点头,让云瑶进了屋,云瑶反手就将身后的门关上了。两人手牵手坐在床上,云瑶的脑袋轻轻的斜靠在世遗的肩膀上,老实说,世遗的肩膀很淡薄。而且世遗特别的清瘦,靠着的时候就是一把骨头,很不舒服,但却很安心,鼻尖吸着世遗身上那淡淡的药香。
“我给你讲一个芸娘的故事吧!芸娘姓陈,夫君沈复,字三白。芸娘自幼丧父,擅女红,全家生计都凭她一双巧手。生性聪颖,自学诗文,亦能写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种句子来。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牙齿有微瑕,更有缠绵之态——沈复说的,估计是情人眼里的西施。
沈复是一个寒士,做过幕僚,经过商,会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写写诗,赏赏画,还有爱花癖。封建社会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有什么伉俪情深,也属于瞎猫逮着死老鼠的侥幸,而且,就算一见钟情,也会有以后那样的惨剧。芸娘因为女扮男装随夫君出游,失去了公婆的欢心,乃至于闹到分家,其实就是逐出家门。好在夫妻感情甚笃,于苦中作乐,依然和和美美,竟然没有应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套路。
芸娘之所以为人称道,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实在太大度了,也不知中了什么邪,绞尽脑汁想给沈复纳一个妾,而且要求还很高,美而有韵。
在两人生活水平只是温饱的情况下,芸娘竟主动考虑沈复的其他需求,纵然沈复谢绝,她依然微笑着物色。
听闻名妓温冷香,便拉沈复去看,结果认为冷香已老,其女憨园正中她意,送了个翡翠钏给憨园,后来憨园给有权有势者夺去,芸娘便大病一场,最后,竟死了。”
“真是个傻女子。。”
望着世遗打着手势,云瑶扬了扬嘴角,是那女子傻呢还是古代压制女人的风俗不好?不管怎么样,芸娘是一个悲剧,但她却又自认为是幸福的。或许是幸福的吧!
“还有吗?”
世遗再次打着手势,云瑶扬了扬嘴角,这个小家伙,今天是听故事听上瘾了?
“好吧。再讲一个,然后你跟着我去吃东西好不好?”
世遗点了点头。
“从前呢有个美人,叫步非烟。体态轻盈纤弱,步非烟工于音律,精通琵琶,更敲得一手好筑,堪称当时一绝。
步非烟由父母作主,嫁给了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武公业身为武将,虎背熊腰,性情骠悍。与心思细腻的步非烟完全是两种人,根本无从沟通。故而,步非烟经常郁郁。
有一日,她在院中赏花,神情萧索,柳眉微蹙,正好被隔壁舞剑时腾跃而起的赵象瞥见,赵象年方二十,长相俊秀,正在家里攻读科举课业——他的朗朗读书声,也曾掠过步非烟的心波,使她伫足墙下,凝神细听。惊鸿一瞥后,赵象再不能忘记步非烟,他重金买通武家的守门人,恳求转达渴慕之情。守门人让自己的妻子去试探步非烟口风。赵步两人经仆人之手,对诗数首,定了情分。终于,机会来了,武公业在公府值宿,赵象逾墙而过,自此之后,武公业不在家过夜,赵象便与步非烟欢会。就这么过了两年,事情再也瞒不住了,风声传到了武公业的耳中,他拷打守门人妻子,逼她道出始末。强压怒火,佯称值宿,伏于墙下,于二更时分抓住了赵象一片衣角,赵象本人跌回自家院落。武公业冲回房内,对正在梳妆打扮的步非烟怒吼,步非烟见事情败露,淡淡说了句,生既相爱,死亦何恨。武公业扬起马鞭,活活打死了步非烟。最后,以暴疾而亡的名义葬了她。
整整两年,作为一个男人,满足于这样的偷。。。情之中,无所作为,甚至连私奔的念头都没有,私奔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不知,那女子淡定从容,不置一辩,任凭毒打,始终不开口求饶,承担了这场孽情所有的悲哀与不幸,她用自己的生命赎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