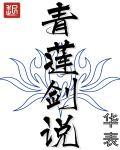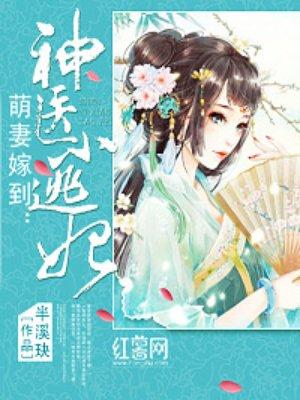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真千金逆袭后哥哥们跪着求原谅短剧在线看 > 第241页(第1页)
第241页(第1页)
她绕过他就走了。她其实不生气,但头一个跳出来的,必须要狠狠踩,以后这种事情才会少一些。众文官的心情有点复杂。这位张大人,后头有人是肯定的,后头的人也很好猜。大家料到了她不会这么轻易答应,但没有料到她这么不客气,更更没料到,她对一些门道这么清楚,含蓄的话听的懂,官场上的事也门儿清,什么“台前幕后姓甚名谁”,这话说的,真叫人心惊胆战!!反正这么一来,所有人都知道了。沈昼锦惹不起。这就是沈昼锦想要的。她富可敌十个国是她的事情,她自己想给,多少都行;但没那个交情你张嘴要,一分一毫都休想;又或者他们觉得给她一点压力,冷嘲热讽一下子她就会主动拿出来?那是提也休提。就算是皇上也不敢下这样的命令,虽然她是这个世界的人,可这都不是你们这个小世界的东西,你们要的着吗?逼急了她说没了,谁又能验证?过了那一拨人,到了武官那边,气氛就好多了。因为像安宁侯,那是正经亲戚,态度极为亲近,她还见到了龙骧卫的副指挥使陆执锐,跟陆执戟长的不像,眼睛没有陆弟弟大,但也有大酒涡。沈昼锦笑跟他道:“陆大人的弟弟一直跟着我干活儿呢,本来这次想带他来的,只是我与小绝都来了,那边还得留人干活,所以就把他和连城都留下了。”陆执锐也是个寡言的,急施礼道:“舍弟顽皮,多承王爷宽厚,一直带在身边教导。”沈昼锦笑道:“无事,我们是朋友,说起来,我还想麻烦一下陆大人,执戟和连城一直跟着我们干活儿,我想给他们讨个身份,不然一直出白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安宁侯在旁,急插言道:“此事不如下官去办。”因为龙骧卫毕竟是皇上直属的,而且陆执锐又是亲哥,放在虎卉卫也好。沈昼锦就道:“也好,多谢侯爷。”安宁侯急笑着应下。沈昼锦发现四卫的将领,都偏年轻,打眼一看好几个都没蓄须,不超过四十岁,虎卉卫的副指挥使闵昭华,看着也就二十来岁,十分年轻俊秀。她眼神一扫到他,闵昭华立刻便上来见礼,寒暄几句,便小心翼翼的道:“听闻王爷擅医?”从没见过这样的作派沈昼锦皱了皱眉,笑道:“说起来,我也得放句话出去……除非是不治之症,否则不要找我,近几年我在京城的时间应该很少,想找我也难。另外就是,我师父,”她比了比身边的沈既明:“我师父并不擅长治富贵病,他更擅长一些江湖中的内伤外伤,或者武道造成的气息紊乱,别的病不要找我师父,没用的。”闵昭华急笑道:“那不知王爷这次要在京城待多久?”沈昼锦问:“你的意思是你家中有不治之症?”闵昭华苦笑道:“正是,家严罹患重病,太医也不知如何治疗。”沈昼锦皱了下眉:“我们那边就停了一天工,我不在就什么也干不了。”后头,霍凌绝的声音道:“请你治病的,以后估计会有很多。”沈昼锦回头,就见一个中年男人,与霍凌绝一起过来了,这应该就是他的便宜大伯,现任的忠肃侯了。这还是头一回见,不过忠肃侯态度极为殷勤客气,两边寒暄了两句。然后沈昼锦就回过头来道:“那就这样,闵大人叫人把令尊大人的脉案先送去我家,我先看看,然后……回头直接在我家门前贴个告示,想让我治病的,可以把脉案送到我那儿,不管我啥时候回来,看到脉案,合适的我就接了,接了之后……譬如文人,病人自己或者子孙,可以给我手抄一卷四书,我拿去卖,又或者可以给我个我看的上的铺面,送掌柜和伙计,又或者可以给我个庄子,送农户和管事。”众人一时哑然:“……”真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派。不过说真的,对他们来说,这种直接摆到明面儿上的东西,比叫人猜可方便多了,而且这是请神医治病的价钱,又不是索贿,所以也没什么好指摘的。不过公然这么说出来,而且铺子还必须送掌柜什么的,就真是叫人不知道说啥了。沈昼锦摸着下巴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另外,如果是有进士功名在身,或者有文名的文人,起码像韩青溪那样有名的,又或者三品及以上的官员,肯给我手抄一套带注释四书的,不管啥病,可以指定一个人我必治。同样的条件如果有人给我抄一套带注释的四书五经,那他的直系亲属和授业师父,我全都可以治一次,调养也可以,当然了,不可能随叫随到,得我有空。对了还有,比如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得自己抄了才算,子侄弟子抄的不算。”这年头名人手抄都很值钱,譬如有个进士,在殿试上可能只是个同进士,不起眼,但在他们本省可能就是个解元,所以他的手抄本拿到他们省去卖,就冲个解元名头就会有人高价买。又如果是余致远韩青溪这种天下知名的才子,抄一套,放到书坊那就是镇店之宝,能卖出天价,关键是显得档次高啊,整个格调都上来了。这年头,混到能进这个大殿的人,基本上啥都不缺了,就缺命。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又聚了起来,然后便有人道:“王爷,若是家人重病在身,来不及抄完呢?”沈昼锦非常奸商的道:“不是本人抄的,可以先欠着,加个利息就行了,本人的可以治好再抄,也要加利息,比如迟一个月多抄一套三百千?”三百千就是孩童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加起来才两千七百多个字,她真是太大方了。一般来说,必然要欠着的。毕竟四书光正文就有十几万,一个朝臣假如一天写个两三千字,就得抄三四个月,加上注释,那就没数了,几十万也有的。五经正文得有五十多万,加注释……简直没法算。除非是没入仕的人,一天能抄十来个小时,抄个几千上万的,那可能抄上两三年能抄完。然后又有文官道:“带注释,以哪本为准?”沈昼锦想了一下,道:“谁要抄,我给你们范本。”这话一说,不止一个文人开口:“不知是哪一家的范本?”这就是文人最关心的一点,沈昼锦笑了一声,道:“博采众长的范本?”这时候的书,当然也是有注释的,甚至还有专门的注释大家。文人会把正经的著作称之为“经”;把注释“经”的文字称之为“传”或者“注”。因为最早对经所做的注,一般都寥寥几句,后来又会进行补充,称之为“笺”;之后又会有人对“传”、“笺”再次注释,就叫做“疏”。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诗经》原来只叫《诗》的,被列为儒家经典之后才叫《诗经》;汉代毛亨为《诗经》做的注释叫“毛传”;后来郑玄又为“毛传”做了补充,叫“郑笺”;唐代孔颖达又为《诗经》正文和“毛传”、“郑笺”重新作注,就成了“孔疏”。而且不止如此。一部古籍,注释的往往不止一家,如果有人把各家注释给汇总了,再加上自己的注释,这就是集解,又叫集释。这么说起来,很麻烦,实际上也确实挺麻烦。对于外行以及初学者来说,就一个字,乱。百花齐放当然是好事情,可这对于后世习惯了“标准答案”和“得分点”的人来说,真的很乱。哪怕你买一本集解,上头一下子看到了三家注释,都是什么什么大家的注释,你倒说说,以哪个为准?为何会如此呢?因为这时候的文人,是讲究家数传承的,很多东西是靠讲解,口耳相传,所以,在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而言,拜一个好先生,才格外重要,而得到师父批注过的书,就是大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