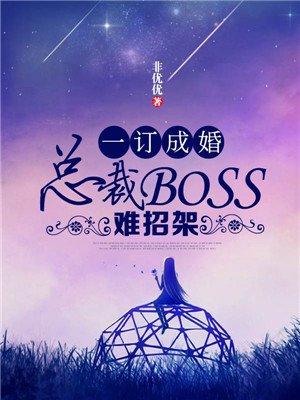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高唐县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梅西的黑色眉毛松开。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有一刻我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我们重新迈出步伐时,她竟然找到了值得笑的事。笑意在她的嘴角若隐若现,脸上或许看不出来,呼吸声却听得出来。
&ldo;听到你最近遭遇的不幸我很难过,&rdo;她轻声说,&ldo;所有的事,我是昨天才听说,当然是听我爸说的,如果我早点知道就好了。&rdo;
&ldo;谢谢。&rdo;我不太领情地说,&ldo;书进行得怎么样?&rdo;
&ldo;还不错。&rdo;她说,语气有点顽皮。
&ldo;但听你的声音,我很难相信你不为任何事而来,准备告诉我是什么事了吗?&rdo;
&ldo;嗯,&rdo;我不情愿地说,&ldo;潘医师认为你或许可以帮忙警察指认一名男童的尸体。如果你不想……&rdo;
&ldo;潘医师?我父亲的朋友,那个正在研究万灵药的医生吗?&rdo;
&ldo;是吗?我以为他只帮小孩看病。&rdo;
&ldo;他是啊,所以我跟我爸才会认识他。没错,就是他。潘医师一直在研究一种能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水配方。他发誓说那是科学,但我觉得太不切实际。有那么多人因为没有新鲜的肉可吃而奄奄一息,治疗方法很清楚旧地在眼前,何必费那么多心去研究神奇药水?可是他为什么会想到我……哦,我懂了。&rdo;梅西叹口气,把提篮往瘦弱的手臂上推。
&ldo;那男孩是本国人吗?&rdo;
&ldo;如果你是指他爸妈是不是在这里出生、有没有口音,或有没有钱打通关卡,我不清楚,不过他看起来像爱尔兰人。&rdo;
梅西的嘴角一斜,对我笑了笑,但跟脸上飞过的一吻一样短暂。
&ldo;这样的话,我一定帮忙。&rdo;
&ldo;为什么是爱尔兰人你就一定帮忙?&rdo;
&ldo;因为,&rdo;她答,再度优雅地避免正面回答问题,&ldo;如果他是爱尔兰人,这城市没有其他的人会想做这件事。&rdo;
指认尸体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我猜这时尸体应该已经清洗干净,包上寿衣,放在王子街和桑树街转角的圣派区克大教堂,离我们只有几码之遥。但第一个问题是,明知道我应该要让梅西看尸体,可是我实在不想让她搭着我的手,走近那面装了五扇窗户的粗糙石墙,通过侧门进入教堂。此外,更大的原因是,这途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暴民。
&ldo;我们要烧了撒旦的宫殿!&rdo;
一名彪形大汉站在一小群模样凶狠的工人面前。彪形大汉身长六尺,落腮胡又黒又密,但看上去不可能超过二十五岁。这些人脸上刻画的风霜都超出他们的实际年龄。这些拥有正当工作的人刚做完屠宰猪只或敲钉子的工作,就穿上自己最好的外套,提着竹蓝,里头装满从河里捡来的小石头,看到爱尔兰人就丢。他们身上的黑色合身燕尾西装和领带夹针很像范伦丁。范伦想要爱尔兰人的票,本土主义者想要爱尔兰人死。这是一群辛苦过活的男人,看他们冰冷的眼神和动不动就握紧的拳头就知道。
&ldo;交给我。&rdo;我对梅西说,示意她到转角等我。
&ldo;你们这些白皮黑骨的家伙竟然不敢面对一个生来自由的美国人!出来陪我们玩啊,胆小鬼,我们会把你们当一袋小狗丢进水里淹死!&rdo;高大青年喊叫着,露出整排牙齿和仔细梳理过的胸毛。
&ldo;今天不行。&rdo;我说。
一双双眼睛转向我,像寄生虫扑向尸体。
&ldo;你是跑腿小狗吗?&rdo;高大青年问,听声音就知道是纽约本地人。
&ldo;我是警察,不是仆人。&rdo;我帮他翻译&ldo;跑腿小狗&rdo;的意思。为了摆摆样子,我把大拇指往警徽一弹,以前我看过很多次范伦丁这样弹纽扣,这是我第一次对警徽油然生出恼怒或厌恶之外的情绪。
&ldo;去找别只想淹死的小狗,别招惹教堂了。&rdo;
&ldo;哦,警察啊,&rdo;那个高个子不屑地说,&ldo;我老早就想扁警察一顿了。这小子口气满大的嘛,看来也听得懂黑话。&rdo;
&ldo;唬人的啦,&rdo;有个看似喝醉的人含糊不清地说,他的脸看起来像被人误认成面团并重新整形过。
&ldo;他只有一个人,也听不懂我们的话。&rdo;
&ldo;丑八怪,我听得懂,而且我一个人对付你们就绰绰有余,&rdo;我呛他,&ldo;快闪,不然我只好送你们进监狱。&rdo;
如我所料,一群人都转头看那个又瘦又长的大个儿。他站出来,双手自然地往内弯。
&ldo;大家都叫我比尔,波勒。&rdo;他低头吹气,味道又臭又重。
&ldo;我是个生来自由、土生土长的共和主义者,无法忍受常备军的存在。信不信老子出手把你打成猪头。&rdo;
他是不是真有这种能耐,我不知道,不过我看得出来他醉了,四肢软趴趴的。所以当他整个身体扑向我,犯了一般高大又臭屁的人常犯的错误时,我移步向前,避开他的拳头,手肘往他的眼窝一戳,比尔先生就像人卸下肩上的麻袋那样,应声倒地。
&ldo;要多练习才会成功。&rdo;我给他良心的建议。他的跟班都跑过来扶他站起来。我又摸了摸警徽,此刻非常高兴有它撑腰。
&ldo;快滚,免得更多个我这样的人赶来。&rdo;
或许跟我老哥吵几次架都值得,只要我能名正言顺地,用卑鄙无耻的方法痛宰别人,我想。这时这群暴民拖着他们的领袖和石头落荒而逃。我拉了拉脸上的绷带,心中的一线希望则是不停地拉扯着我的脊椎,毕竟梅西就在我后面。梅西‐‐不在我后面。教堂的门开着,呈现出门框优美的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