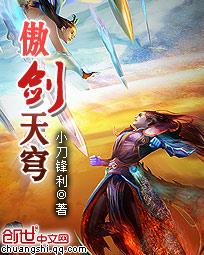天天文学网>唐朝凌烟阁24功臣都有谁 > 第58章 行走在刀刃上的宇文化及(第2页)
第58章 行走在刀刃上的宇文化及(第2页)
在隋朝的官员中,黄门侍郎裴矩最有眼力劲儿,其心思缜密且老于世故。他提前预见到会发生动乱,因此他对待即便是最卑微的仆役也极为仁厚,前文我们讲过,他还提出建议,让骁果军士兵可以在江都娶妻成家,甚至可以纳妾。这看似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骁果军士兵大多是远离家乡的精锐力量,为他们娶妻,让他们在京城有了家庭的羁绊,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军心,减少他们参与叛乱的冲动。
等到动乱爆发后,这些士兵心中对裴矩确实存在着一种别样的情感。众多叛军口中都传出这样的话:“裴黄门(对裴矩的尊称)没有什么过错。”
随后,裴矩看到宇文化及后,远远地就毕恭毕敬地拜倒在马前,可谓马首是瞻,他的这个举动让宇文化及觉得他没有威胁,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另一位在叛乱中幸存下来的是苏威,他是隋朝的重要政治家和法律家,苏威出生于北周,是西魏度支尚书苏绰之子。他五岁丧父,继承美阳县公的爵位,任郡功曹。苏威主持修订了隋朝的法律《开皇律》,为法制整备做出了重大贡献。
苏威在朝廷中的名声和地位一直很高,平日里多忙于处理朝廷的各种事务,对于朝廷内部的权力争斗和阴谋诡计并没有过多地参与,所以在宇文化及等叛乱者眼中,他就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边缘人物。
宇文化及因为苏威未曾参与杨广朝政,也赦免了他。
宇文化及政变成功后,百官都前往朝堂道贺。
苏威看到形势已定,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前去拜见宇文化及。因为苏威的名声在外,他前去参见宇文化及时,宇文化似乎想借此展示自己的大度与威严,便召集众人出了府门迎接他,对他礼遇有加。
这个时候,按照常理来说,百官都应该到朝堂去表示祝贺宇文化及成功掌权,尽管这是一种扭曲的“祝贺”,装装样子的无奈之举也罢,在这种形势下,去了总比不去强。
然而给事郎许善心却不为所动。他心中有着坚定的忠君思想,对于宇文化及这种篡位夺权的行为深感不屑和愤怒,只有他没有到场。
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今河北省徐水县)人,是中国隋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南朝陈和隋朝两个时期,以其才华和忠诚着称。此时他已六十一岁。
许善心九岁丧父,由母亲范氏抚养成人。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十五岁就会写文章,被称为“神童”。许善心最初在陈朝任职,历任新安王法曹、度支郎中、侍郎、撰史学士等职。隋朝统一后,他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如秘书丞、礼部侍郎等。许善心着有《神雀颂》等文学作品,其文采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他续成了父亲许亨未完成的《梁史》,并编纂了《七林》等图籍目录,对后世史学具有很大贡献。
许善心的侄子许弘仁看到叔叔没有前去朝堂参拜新“掌柜”,急忙骑马来劝说许善心:“天子已经驾崩,宇文将军正在摄政,满朝文武都已齐聚。天道与人事自有其更迭的规律,何必过于忧虑,叔父而如此徘徊不前呢!”
许善心听后大怒,坚决不肯前往。
许弘仁看到许善心如此坚决的态度,只好转身骑上马,感慨于叔叔的忠义和执着,想到叔叔可能会遇到灭顶之灾,不禁伤心地哭泣着离开了。
宇文化及听到许善心如此不懂人情世故,心中十分恼怒。他觉得许善心这种公然对抗自己的行为是对自己权威的严重挑衅,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且辜负情义的行为,便派人到许善心家中将他捆绑到朝堂之上。可是,也许是宇文化及想要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不久后又释放了他。
许善心从朝堂出来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宇文化及表示顺从之态,未遵循朝堂之上的礼仪,未向宇文化及表示不杀之恩,不行礼就直接出来了。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宇文化及,他觉得许善心是故意在众人面前羞辱自己,让自己下不来台。宇文化及愤怒地大声说道:“这个人真是太傲慢无礼了!”
于是再次下令将许善心捉回并杀害。
许善心死后,他的母亲范氏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高寿之人是家族的珍宝。当她得知儿子为了国家大义而死时,她虽然悲痛万分,但表现得极为坚强。她来到儿子的灵柩前,并没有像常人那样放声痛哭,也未流下眼泪。她只是轻轻地抚摸着灵柩,平静地说:“能够为国家死于危难之中,我能有这样的儿子,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说完,她便躺在床上,茶饭不思,十多天后,也追随儿子而去。
担任千牛左右(同千牛备身)的张琮,他同样也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不愿意屈从于宇文化及的叛乱统治。所以,宇文化及毫不犹豫地杀掉了他。
张琮有两个哥哥,大哥是张季珣,在李密、翟让攻陷洛口仓城时,张季珣坚守不降,与李密军队进行了长期的对峙。最终城陷,被翟让所杀。二哥张仲琰在唐王入关时,率领吏民坚守上洛,最终因部下背叛而被杀。就这样,张家兄弟三人,都先后为国家死于危难之中。他们的忠义之举,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得知他们的故事后,都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到悲痛,同时也对他们的忠义精神感到钦佩和惭愧。
之后,宇文化及对外宣称,依据萧皇后的命令,立杨广的侄子秦王杨浩为为傀儡皇帝,让杨浩住在别宫,仅负责颁布诏书和敕令,不得干涉政事。同时派遣士兵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宇文化及自封为大丞相,总管百官事务,拥兵十几万。他不顾朝臣和百姓的感受,强占萧皇后,他还把六宫妃嫔占为己有,完全无视伦理纲常,跟隋炀帝杨广一样荒淫无道。
宇文化及的名字“化及”取自“化育万物,兼及众人”之寓意,与《论语》中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思想有相通之处,都表达了希望个人能够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影响和改变周围世界的愿望。但遗憾的是,他的行为并没有践行这一美好的寓意。
宇文化及又任命他的弟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司马德戡被封为光禄大夫,温国公,后又升到礼部尚书。
宇文化及封了百官爵位,开始宣布江都内外戒严,并宣称计划返回长安,赶走李渊。同时他还继续徵兵、征税,毫不手软,导致江都地区民怨沸腾。
宇文化及的暴动叛乱的行为,本质上是赤裸裸的权力篡夺。他在江都这个隋朝的重要据点,封百官爵位,这一举动完全无视隋朝的正统统治秩序。他妄图通过这种手段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体系,以满足自己的野心。这种行为反映出他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下,这是一种典型的乱臣贼子行径。
他接着宣布戒严令,本身就带有一种高压统治的意味。而继续徵兵、征税毫不手软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在隋朝末年,百姓已经饱受战乱、苛政之苦,江都地区也不例外。他的这些行为使得原本就脆弱的民生雪上加霜,必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和抵触。民怨沸腾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最基本的统治根基,民众不会支持一个只知压榨他们而毫无建树的统治者。
而且,宇文化及宣称“要返回长安赶走李渊”看似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实际上是非常盲目的。李渊当时已经在关中地区建立了相当稳固的势力,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宇文化及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后勤保障以及李渊的军事应对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仅仅凭借着一时的冲动和所谓的“正义性”(当然这种正义性是站不住脚的)就妄图发起征讨,这是一种缺乏战略眼光的决策,也可能连“战略性”都称不上,只是为了稳住众多想要“回老家”的将士的心。一个生性怯懦之人,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权体系,又会有多大的作为呢?